一九六八年冬,十二月二十二日,书友慧德挚意带我去见一个人。他说此人与庸众的读书人不同,不但睿智聪慧,而且思想深邃,有自己的见解,不随世俗,人更俊秀。那时我潜心研究哲学,作搬运工,对顶峰论有质疑而被当时的读书人所共知。晚六点下班时已蓬头垢面,满目灰尘,一身褴衫。慧德带我到达河医家属院老八排平房时已晚七点有馀。有一间半平房,在平房的半间见到了要见的人—张宏锦。她一脸英气逼人,气宇轩昂,仪态严峻,清秀的脸上镶著黑而亮的智慧的双眼。黑夜给她以黑亮的眼睛,她用来以寻找光明。坐定後,她一语惊人:“我在思考客观世界和物质力量对社会形态的制约,而你对哲学有如此大的兴趣,为什麽?”“哲学不止一种,世上有各种哲学,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哲学、纪院哲学、启蒙哲学、思辩哲学……各种哲学用各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认识与揭示世界,问题在於改造与改变世界。”木讷的我好像在背书。“一个时代问题的症结衹有存在於它的政治经济领域里,空空的哲学怎麽能找到答案?又怎麽能改变世界?”又是有力的反问。“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 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 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 要能说服人,就能 掌握群众;而理论 要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 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这回真的是在背书了。“人为环境与教育的产物,而你认为,仅仅靠意识形态,人们能够解放自己吗?”她尖锐地问。“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内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当然是在背书,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结论。谈话在逐步深入,双方兴趣盎然,我们对当时社会的一言堂有共同的感慨,於是我颇有感触地诵出马克思论普鲁士出版法的精彩段落:“大自然是五光十色、万紫千红的,水珠在阳光下闪烁著光怪陆离的颜色,玫瑰花与紫罗兰在空气中有著不同的芳香,而你们为什历 准出版界有一种色彩—即普鲁士的官方色彩呢?”又是在背书,我注定是书呆子。她的眼睛闪烁著光芒。这时我注意到书桌上放着几本伟人传记的书,便问道:“你喜欢读伟人传?”她点点头,我便脱口而出,“伟人之所以看起来伟大,是因为我们自己跪着,站起来吧!”她欣赏地看着我,若有所思。这时她母亲走了进来,慈祥、矜持而有贵气,对我们微笑。而我还在旁若无人地侃侃而谈,还是慧德替我向她 母亲问好並饶有兴趣地与她聊了起来。
另一房间与此房相通,坐满了那时代的知青,大都是她哥张宏时的同学,她的父亲张静吾坐在那里,我看到他正示意往这个屋里的人倒茶,向我示意喝水。他父亲站沉默无话。第一眼看上去就感到他颇有阅历,是一位长者的风范。後来知道他名张静吾。四年之後,在第五个年头的夏天,他成为了我的岳父。我与岳父的第一次见面是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没有一句言语与寒暄。後来知道那年他已六十八岁。而我二十岁,一个初出茅芦就挥舞著进攻的长矛的人,不谙世事,唯知思维与批判旧世 界,言必称思想的解放,动輙则说旧世界的庸人云云。後 来宏锦告诉我,第一次见面後母亲说:“那个低个(指慧德)聪明、懂事、灵活,那个高个(指我)好像在背书,是书呆子,一讲话就自以为是,目中无人,骄傲自大。”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风和日丽也好,风雨如盘也好,大抵都如流水。我第二次见岳父时,是在一九七一年初冬。是宏锦告诉我老人要到郑州开会(当时已调入临汝温泉工作)。省里召开爱国人士座谈会, 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会後,在河医门口的水果店见到他。他还是穿着一身藏青色的旧的中山装,衣兜内装有两个大方格的手帕,他告诉我可做春天包樱桃用。樱桃是一年中的第一种水果,很好吃,还讲到秋天,手帕可以包桃子,桃子也很好吃,在老家巩县,可以包柿子的。此时的他,心中有 几分喜悦与舒展。他告诉我:“此次会议与张軫一块,张 軫,旧军人,後起义,担任过国家体委副主任、省政协 副***。人耿直,此人与我一样,在五七年後成为大右派。”我此时对眼前的这位长者肃然起敬起来,不知道讲什麽话为好!在此前几年,我曾细读了许多五七年的反右丛书,字里行间知道他们都很有思想,满腔热忱、有见解,为了国家与民族的进步敢於直言坦言,讲出了真话实话心里话而遭到了厄运,而在现实中还没有见到过一个右 派,何况是一个大右派,眼前的这位颇具童心的长者! 我开始仔细打量这位慈祥的老人,他思维敏捷,学识渊 博,並不仅仅局限於他的医学,他识人识事识物,论及 世事与世人,与其说入木三分,不如说入骨三分。他讲话极有分寸,怎麽也看不出他会有右派的慷慨陈词、铮铮有力的声音?我在思量著他,而他分明在经过五七年的风云之後,无论从论世论人论语都很有分寸了,对敏感的话题从不越雷池一步,对任何人从不妄加评论。我讲章伯钧、罗隆基,讲钱伟长、费孝通,他很慈祥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话说多了,人就要吃家什!”
我第三次见岳父时,是一九七三年秋,他在临汝温 泉,即河南省幹部疗养院,那时河医备战疏散於此地。院 落乾淨整洁古朴。西院是医院的门诊部,东院是平房的家 属院。我与宏锦已成过婚,住郑州嵩山路南段,我们是专 程去看老人的。秋日的骄阳照耀着掛满丝瓜的屋簷,屋簷 内就是岳父岳母住的地方,虽地处穷乡僻壤,房间内却井 然有序,餐桌上依然是精緻的嘉庆斗彩瓷盘,盛满了榨菜 肉丝、光绪粉彩小碟里盛的是酱黄瓜,青花釉里红汤碗中是美味可口的鸡丝面……。岳父这次健谈了起来,他说人 到一地,先要看看四週的环境,看明白後才能安下心来。 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把温泉疗养院四週的农村全转遍了, 使我感到莫名惊诧的是,岳父每到一个村庄,总有许多乡下人与他先打招呼,问寒问暖,亲热如老朋友。我问怎麽认识他们呢?岳父严肃起来,很认真地说:“马大值钱大,人架子大不好,既然入乡随俗,我就要与此地的老乡和睦友好相处,与他们做朋友。我们医院也有不少教授, 不理人家、不理老乡,彷彿高人一等,自己作一个教授有 什麽了不起?你就不吃老乡种的粮食、蔬菜?我不信。一个学医的人怎能不与老乡、不与农民打交道呢?学医是为 什麽?为了给人治病! 教授是人,农民也是人,何况我们国家百分之八十都是农民……。”我感到岳父话里蕴涵了深沉的真理,他学医的夙愿是为了多数农民,为了医治满目疮痍的人间疾苦,不是为博士院长的头衔、也不是为一代名医的声望,而是解除民间疾苦。学医为济民,是不为良相、但为良医的传统儒家思想的延续与承继。此临汝之行,岳母没有再称我是不懂事的书呆子,更没有记起讽刺人的旧嫌,而是亲切地夸我走路的姿势像刘老五,大气
魄。那年,岳父在温泉疗养院西院的阅览室,他兴致勃勃地让我到那里参观,而宏锦在家中陪母亲包饺子。回家的路上,我听到岳父在低声地哼著京剧,是《红色娘子军》中的一段,广播里的高音喇叭也是在放这一段:“娘子军 连歌天天唱,今天唱来格外亲,今天唱来格外亲……。”
一九七四年的深秋,岳父岳母从临汝温泉回到了河医,住在院长楼旁边的平房里。相处的日子逐渐多了起来,而谈话的内容也相应的多了起来。岳父看到报纸登了章士钊先生到香港不久就去世了,活了九十三岁,人称老虎总长,“老虎总长是何意?”岳父分明是在考一考我。“大约二十年代章士钊办《甲寅》杂志,主张国学为本,章士钊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任段其瑞执政府教育总长,甲寅为老虎。所以世人称他为老虎总长。”我历来钦佩鲁迅先生而偏视章士钊,尤其是读了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论费厄波赖应该缓行》之後。岳父看透了我的思想倾向,很耐心地说:“此人很有学问,国学造诣很深,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每每为座上宾,我二十年代在北京德国医院时,在京华就闻其名。青年人看历史不可偏执啊!”岳父继续说:“人被涂上政治色彩是出於无奈, 並不是一个人的本意。青年时很难理解。我过去在抗战时 期作军医院的医生,接融过不少军人,其中有一位原东北 军出身的少将,很有才幹,在滇缅战场打了不少胜仗,与 他同一军衔的人都升为了中将或上将,而他依然还是少将,我问他何以致此?他说他过早地涂上了政治色彩,很难抹掉,也很难摆脱掉的,无可奈何……”若干年後,尽管仍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本是自由人的豪气,尽管人生又开辟了新的领域,开拓了新的境界,尽管我在高等院校的教书生涯中怡然自得运用自如,但细品岳父以切实的例证讲述的人生哲理,感慨油然而生,其中告诫之可贵唯心灵深处方可感知, 惜年轻时不更世事,难以领略岳父之谆谆教导罢了。
後来,郭沫若出版了《李白与杜甫》,我买了一本赠与岳父,知道岳父故乡与杜甫诞生地仅一里之遥。在此之前曾背诵杜甫的《赠卫八处士》诗,岳父很喜欢这首诗,说:“杜甫访旧半为鬼,惊呼热衷肠,我是访旧多为鬼,惊呼热泪长了。”我对郭沫若臆断李白出生在中亚碎叶很有质疑,而岳父对郭沫若扬李抑杜的思想深表不满。岳父说:“杜甫是人民诗人,其三吏、三别在青史上独放光彩,为世人公认,谁能写出这样洞察现实充满人间苦难的诗篇?只有杜甫,在巩县瑶湾出生的杜甫!我对杜甫有感情,郭沫若说他什麽门阀观念,我心里不高兴!”时代不 幸诗人幸,话到沧桑语便工。历史与诗史的辩证关係大抵 如此,诗人在生活中的际遇与诗人在文学史上的造诣也大抵如此。
论及历史,他说:专制制度要的是奴才,而我们民族需要的是人才,奴才只会听话照办、亦步亦趋,而人才 方能继承创新並开拓历史。他从不妄言,从不人云亦云, 他是一个不唯上不唯书只为实的人。论及世事世人,他每每流露出胸阔似翰海,常怀赤子心的真情,尽管他历经沧桑又饱经磨难。他兴致勃勃地谈起二十年代留学德国时期的武剑西、孙炳文、房师亮、***、史逸等人……他对马覆庭如何说服他离开京华到河北大学医学院任教授记忆犹新……讲上海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知人善任,让他全权代 表同济大学医学院並承办第一重伤医院……讲武汉同济医 学院梁之彦教授胃口好,见解也好,学识渊博……他高兴的回忆张建创办贵州安顺军医学校让他筹建附属医院的情景,张建为人豁达大度、胸有成竹……他睿智、诙谐、率真的秉性时时在回忆的叙述中自然流露出来,当一句插话可以引发他的共呜或引起他大笑时,他锐利的眼睛快活地嘲弄地闪动起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辛亥革 命老人、孙中山的保健医生上官悟塵是岳父常常惦记的至交老友,岳父说他风流倜傥、卓而不群,可惜晚年孤 单,常以长生果相寄,上官老人寿辰103岁……在京的前亡妻吴芝蕙之弟吴黔生多年疾病缠身,岳父不断给他汇款,接济其生活……岳父的心中对人间充满了诚挚的爱心。
岳父个性的另一面即刚直不阿、正直无私、脾气暴戾为医学院老同事所熟知。如一九四九年前曾慷慨陈词於军政部军医总署,勃然大怒、驳斥种种旧论,力陈全国医学院承建重伤医院的必要性;一九四九年後大发雷霆於河南省卫生厅,为了一台进口设备没有安装在河医附属医院。他经常不定期检查病房,使所有医护人员提心吊胆,称他为“警铃”。不知道岳父发脾气时是什麽样子?记得岳母曾给我讲起过老河大医学院的人哄小孩时说:“不要再哭了,不要再哭了,再哭张院长就要来了”……。然而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没有看到他发过一次火,没变过一次脸,他是一个温和的长者、一个慈祥宽厚的父亲。记得他八十八岁时,外出後归来的他,看到整个房间都是他不在时被调换了,他沉默不语,他只讲了一句低沉的话:“今後,我说的话还算不算一句话?”在与岳父的谈话中,我常常与他争论。我是一个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的固执己见的人。而岳父在与我的辩论中则常常耐心诱导,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真城地感化我。他说:“心贵平和,情贵澹泊,激情、激动对神经对 心臟都不好,慢慢就会懂得……何況,人在争论时一定要 以佔上风为快吗?”後来,宏锦开玩笑地告诉我说:你再 与爸爸谈话争论,假如把爸气病了,我们全家都会一起找你算账。殊不知,若没有争论,没有争论的兴致与雄辩,也应是人生的悲哀。
岳父爱收藏鉴赏。傳世的有二十四史木版本、《皇清 经解》、《王船山全集》、《佩文韻府》、古版《昭明文 选》及其他各种子集,约有千馀至两千册。还有古版《纪事本末》、《中州名贤文集》,其中《歌德全集》、《席勤全集》、《世界文库》,在中原以至国内也为罕见。岳父喜爱宋瓷,尤其是北宋汝瓷、北宋钧瓷、北宋汴京官瓷,均存有几件。岳父的故乡巩县是北宋皇陵所在地。岳父更酷爱书画,收藏有唐寅的画、康有为的字,华世奎的书法、谢瑞阶的画作,尤爱“欲除烦恼须无我,历经艰难好作人”的书法条幅。一九七四年冬,岳父把几件宋瓷都 赠与了我。他深知我崇拜宋代文化並珍爱宋瓷。岳父曾是 北京德国医院的第一位中国医师,也是唯一的中国医生。二十年代的国人,崇尚德国医学,京华更甚。由於岳父医德秉正、医术精湛、名震京华,加之德国国家医学博士的头衔,求医求救於他的民国要人、满清遗老遗少、君主立宪党人络绎不绝。被他治愈过的有:梁启超、吴佩孚、郑孝胥、奕亲王的後裔、张廷芳,以及精於收藏的刘镇华、张伯英等人。他绘声绘色的叙述,栩栩如生,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岳父畏寒,每年冬天,他总是亲自動手把爐子生起 火来,不管是在平房还是在院长楼,从来不指望暖气。他手里拿着勾火炉的铁长钩,在不停地敲击著炉子,在检查哪里可能漏煤气。其敲击的动作十分认真而又十分可爱,一边敲击,一边在说:“每年没有冻死者,却有煤气中毒 者,中毒者在於其不严谨,不注意爐子漏气,把一氧化碳 弥漫於室内,生活中无处不科学啊!德东你生活中很粗心,更要留心!”……每每忆起岳父的这席话,一股暖流 充满全身,热泪夺眶而出……
每次与宏锦和孩子们一起到河医看望父母,宏锦总是帮母亲做家务,而我的任务就是与岳父聊天谈话,作食客,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无所不及。岳父虽也乐在其中,但对我仍保留著不同看法。终於他把对我的洞察以玩笑方式说出。一天他对我儿子说:“启启,回家问你爸爸,火车为什麽会跑?飞机为什麽飞上天?”……时间久了,他老人家就对我直言说:“你研究哲学、人文社会、历史与改革、博览群书,这都很好。如果能用点心思研究 人与自然的关係,做些实事,才能成为更有用的人。”岳 父的话一针见血,指出了那个时代具有理想有政治激情的年轻人的通病。从那时起,我才开始潜心读英国李约瑟写的科学技术史,读自然科学史,注重一个时代的生产力的发展与体现这一时代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工具。
適逢華裔美籍學者韓誠信夫婦堅持要到河醫看老師,嶽父一家搬進了院長樓,有樓上樓下,六間房子,這在當時是省會最像樣的住房。嶽父在樓上有了自己的書房,傍依著金水河兩岸垂柳下的流水;枝葉茂盛的法國梧桐樹遮闢著窗口的驕陽。這幾年,在主持院務、主持院學術委員會、主持學院學報忙碌之馀,常常漫步於金水河畔,有時漫步於校內大操場,沈思、回溯,猶如盧梭所述是一個孤獨散步者的遐想,幾年後構成了《九十年滄桑》……。嶽父的本意並非出版,衹是給家中後人一閱,以陳述自己的心跡與人生曆程。
河邊垂柳知春早,高山勁松能耐寒。仰府萬物皆更新,滿腹滄桑誰共言?斜陽外,古道邊,夕陽山外山,自信人生二百年,滿腔熱血報祖國。在時局危難中,率領第五重傷醫院,冒著烽火硝煙,搶救傷病員,容納六佰馀傷員的大醫院,輾轉於上海、蘇州、太湖、宜興、蕪湖、宣城、九江、南昌、金華、贛州、吉安,迂迴曲折,九死一生,細算起來,豈止三萬六千裏?東渡日本,學醫濟民……遠赴德國歌庭根大學、慕尼黑醫學院……莫斯科紅場的足跡,巴黎凱旋門與埃菲爾鐵塔下的遊覽……蘇伊士運河入地中海,從馬賽港到裏昂,從裏昂到巴黎,從巴黎到柏林,再到歌庭根城……歸來時仍乘法國的波多斯號大郵船……天之涯,海之角,如今棲身於金水河岸……知己同窗,多已凋零,人生事業、幾度輝煌……世態炎涼、人間依舊真情在,幾多磨難?……幾多坎坷?……幾多徹悟?……幾多蒼涼……。是全然化入筆墨,還是給後人留下懸念?匪夷所思也,匪夷所知也。“大雪滿天地,何爲仗劍?欲談心事,同上酒家樓。”房間裏掛著書法家寒江寫的頗爲晗恿的詩句,
也耐人尋味。世事難,行路難,而寫書更難,大概有如此……
一九八五年九月,過了生日之後,嶽父突然患急性膽囊炎。假如搶救不及時則不堪設想。他的弟子們在河醫的各科大都成爲了名教授。在討論如何急救老師。外科著名教授石炯一語破的:“立即給老師做手術!老院長的病刻不容緩!”蘇壽恒、謝志征、許佩欽教授親自持刀,把手術做得乾淨、利索,十分成功。而在手術室的外面,魏太星、張效房、李振三、吳國桢、蘇壽泜,張延榮等名教授都在急切著結果,一直到老院長安全順利地從手術室推出來……又多次到病房看望慰問。父親康複後健康仍然如故,精神依然矍铄,依然興致勃勃地參加各種會議。每逢春節,他的學生們常結伴到家中給他拜年,這些學生也多爲醫學院的專家和名教授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嶽父是醫學泰鬥的稱謂是醫學界同
仁所公認的。是七十馀年學醫的曆史造就的客現事實。醫學史已留下他的英名與篇章。
一九九二年五月,岳父九十二高龄,在参加过省里会议後,由於神经劳累过度,精力高度集中,这些诱发因素导致了岳父在会议後的第二天患了脑血栓。抢救後入高 幹病房102室以待康復。宏时、我、静宇,三人轮换值夜 班,家里其他人值班。一月後,右手与右下肢瘫痪,而他思维与意识、语言讲话,都如以前一样清晰、有条不紊。我值班时,岳父清醒地告诉我:“人得脑血栓,是很难康复的,我从二十年代在德国歌庭根大学、慕尼黑大学就学习研究神经内科,至今世界各国尚无人攻克此课题。衹有逐渐等待死亡,他们衹是死马当作活马医罢了。”“也不尽然,十三年前,你因食物中毒住院,吃牛肉,拉肚子,你就说不行了,与你的同乡杜甫一样,杜甫当时是“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没有医院可治疗,衹有撒手人寰。而你现在处境与他相比是霄壤之别。当然会康复的!”我信心十足地说。“德东,你不懂医学,神经的康复是很难很难的啊……”岳父又说:“二十二年前,在临汝,那是冬天,下鹅毛大雪,我感冒高烧引起肺炎,你岳 母带学生实习,家中无人。是当地老乡们把我抬到了医 院,假如不是及时彻底治疗,二十二年前我就去见张仲景了,还能与杜甫谈诗。”是啊!当人被病魔折磨得痛苦不堪时,谁都会想到死,然而死並不是解脱,死衹是给自己 带来轻鬆,给亲人和後人们留下无尽的痛苦和怀念。“刚 才,我从走廊过来时,张仲景让我转告你:‘坚决不见张静吾!’”岳父听後大笑:“你有时很可爱,多时不听话,很固执己见,更不热爱劳动。我就不赞成你教育孩子的专业方向,一个学美术,一个学音乐。要知道一个民族连自身的衣食住行都没有解 好,怎麽能有心画好画?学 好音乐?我是不懂啊……”此时,我心中也充满苍涼,怎 麽表达才能让饱经沧桑的老人不失望呢?要知道在他心中是想让下一代学一个扎扎实实的立足於现实的专业!先谋生、後谋事。平心而论,我与宏锦都不现实,在人们眼中包括家人的眼中都认为是好高骛远的人,不务实的人。是的,我历来以务实为羞,我历来是追求超越现实的理想的唯美主义者,致力於抽象思维。我的心愿是让儿女们能从事一种超越派争、超越政治的纯学术的专业,不分地区、不分种族,也衹能是美术与音乐了,它是艺术,是人类共同的美好渴望与不懈的追求。面对岳父的关切,我沉默不语……
後来,宏锦出国留学深造。我带儿攜女奔波於上海, 在宁设机构,展转於沪宁杭之间。儿女以傑出的成绩昂首 阔步跨进上海高等院校,上海成为我心中所繫的地方。无 形中我疏远了河医,疏远了多少年来以此为家的心中家园。每每隔很长时间,才到河医家中,岳父见我从无怨言,总是关切地问:“刚从上海回来?两个孩子怎样?学院的伙食好吗?”岳父已经慈祥地坐在轮椅上。生活依然有规律、整洁,作息时间固定,吃饭定时定量,从不多食,饭後必漱口,牙齿保护完好整齐,连一颗都没有掉!在九十八岁高龄的这年四月,当春意阑珊、杨花似雪飘落满地的季节,岳父还坐轮椅到河医学生宿舍楼下,他静静地观望学生们的生活……我看他陷入沉思,犹如看到他当年在德国歌庭根大学留学时的峥嵘岁月……
当年五六月,岳父因老年性前列腺炎患尿潴留,住 203病房,见宏时守在身旁,後来又去,见宏改在守护。那时岳父已很消瘦,慈祥的面容依旧在关切地问:“两个孩子怎麽样啦?”当我说两个孩子在上海发奋读书、学业专业都很优秀时,他欣慰地笑了。同年八月十一日,岳父因感冒、肺部感染住进河医附院抢救室,住院的第一天低烧,第二天发高烧,第三天已处於高度抢救之中,终因呼吸衰竭於一九九八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一点三十分溘然长逝,终年九十八岁。记得一九七四年冬日围炉烤火时岳父在偶然谈话中说:“我患过肺部的 病,曾几次戒抽煙,肺部不好,早晚会因呼吸衰竭而告 终。寿可傲王侯!但人的病竈很难根除!”神有神灵, 医有预感,人有感应,果其如此乎?
秋雨、酷夏、寒冬,晨雾、夕阳……岁月一天天的流逝,人亦一天天的苍老,从一九六八年冬第一次见岳 父到如今,四十年岁月过去了,当年那个冲決罗网的狂 飙式的、那个叱咤风云的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已经变成年迈花甲之人,定居於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我终於回郑,佇立在岳父的墓碑前……岳父的身影与那藏青色的中山 装都闪现在眼帘……彷彿是梦幻,岳父的音容犹在:一 皱眉、一挥手、一笑谈……一碟肉末、一份月饼、一顿 水饺、一碗棕子、一盘水果、一盃茶水……河医温暖 的家,其情其境,又历历如绘地呈现在我的眼前,四十 年犹如一片煙雾被一阵急风驱散……彷彿又是一九六八 年冬天的第一次见面……远处一片萧索,天空仍旧是灰蒙蒙的,仰望天空,天空阴沉,空旷无语,俯看中原大地,大地一片寂寥,沉默不言。《圣经》说:人死後灵 魂可以昇入天堂,中华民族的历史也认为人死後有灵魂 的,谓之九泉下有知,谓之在天之灵。岳父衹是在墓碑下静静地安息罢了。人辛苦一生总要有安息之日的。生与死、死与生,本相对而言,相反而相成,互为区别,又互成各自的概念。
岳父虽死犹生,音容宛在……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时、阴雨霏霏,记忆中的金水河畔的杨柳已不复存在……河畔的老八排平房早已荡然无存……而记忆中的岳父依然是一九六八年冬的一身藏青色的中山装,依然是满脸皱纹……依然是坚韧不拔、自强不息……他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整个说来,再也见不到像他那样的了……伫立在墓碑前的我在默默地为岳父祈祷……长歌一曲,慷慨悲歌,悼念父:
伊水泱泱
北邙苍苍
河洛文化
蕴吾无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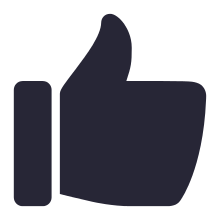








小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