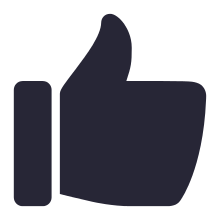其实,对于这位从小就认识的和蔼可亲的高院长伯伯,我到现在还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在我小的时候,他就是我父母工作单位十九冶职工医院里德高望重、一言九鼎的老院长了,而且与我家里的关系非常密切,他的两个儿子还是我儿时的好大哥,一个叫做高伊凡,他曾经是我父亲科室里的检验医师,算是我父亲的半个学生兼同事;高院长还有一个小儿子叫高翔,我还叫他为三牛哥,上世纪八零年代初的时候,他还利用出公差的机会,带着我去爬过峨眉山呢。后来,高院长一家人因为工作调动,先是去到了江西省的鹰潭市工作,后来又去援建当时刚刚兴建的上海宝山钢铁厂(即现在的上海宝钢),如今他老人家早已经离***赋在家,安享着他优渥幸福的晚年了,估计他现在应该已经是九十多岁高龄的老者了。值得高兴的是,高院长到了如此高龄,依然还四世同堂、健康幸福地活着,已经是实属不易了,这也许与他当年的那些善为和积德不无关系,衷心祝他老人家健康长寿!就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我曾带着哈佛钢琴演奏家TONY小子到了上海音乐学院开钢琴独奏音乐会,高院长的长子伊凡哥还专门与我通了一次很长的电话,本来说是要专门来上音观看演出和见一下我的,后来因为他临时有事而未能到场,很是遗憾!如此算下来,自从我离开了我的第二故乡攀枝花之后,我与高家的那些亲人之间已经有三十多年未曾谋过面了,下次若是再有机会去到上海的时候,一定要设法抽出时间来与他们欢聚一下,好好地叙一叙旧情!这位德高望重的高院长尊名叫做高国新,我是一辈子都会牢记和感激他的!有一件很有意思的往事,是我父亲与高院长两个人长得很相似,面容宛若是一对失散过的亲兄弟重聚一般!曾经有一位住院的病人在康复之后,回到医院来感谢他的救命恩人,竟然在医院的走廊里就拉着我父亲的手连声道谢,还是口口声声地谢谢高院长!我父亲一再解释说自己不是“高院长”,可那个病人并不以为然,固执地说“您就是高院长,您的救命之恩永远不忘”云云!可乐吧?从这个小故事里,我能感受到的,可能并不仅仅只是我父亲与高国新先生之间的友情,更能领悟到的,还有中国人的一句至理名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也许,正是命运之神的巧妙安排,让我的父亲与高国新先生在人生的旅途中相逢、相知和惺惺相惜吧?
高国新先生
就在本次的博文连载即将发表的前夕,我因想讨要一张高院长的照片而与伊凡哥又通了一次电话,结果出乎我的意料,我不但求到了高院长的彩色旧照,还获知高院长本人也是老四野林帅的部下,还是著名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军三十八军虎将梁兴初、刘西元麾下王牌劲旅113师的军医!如果再往前历数的话,渊源就更深了!原来,高国新先生还曾经是是原国民党湘军名将陈明仁将军的旧部。更为巧合的是,当年成功策反了陈明仁、李立三弃暗投明阵前倒戈起义、和平解放了长沙古城的主要策动人和新中国大功臣,就是我大姨父的父亲、原新中国成立后的湖南省第一任省长程星龄先生,这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虽然我的父亲与高国新先生同属于林帅麾下的解放军四野,但他们在国内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并不相识,只是在各自集体转业之后,才在武钢的“大熔炉”前会师相见了!说起来,高国新先生在担任我父亲单位里的医院院长之前,曾经追随林帅及梁兴初将军等解放军猛将们,在历次的大型战役、剿匪及抗洪抢险等革命工作中,屡获殊荣!他不但曾获得过特等功的勋授,还在一座由***和周总理亲笔书题的人民功臣纪念碑上,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大名!也许正是因为曾经同在老四野林帅麾下服役参军的经历,他与我父亲一见如故,结下了十分深厚的革命友谊!所以,当高院长发现有一位淑雅漂亮的湘女大学生来到医院工作时,立即想到了彼时还是单身的我父亲!于是,我父母的那一场旷世难觅的“天作之合”婚恋,就此顺理成章了!因而,我在今天的这篇纪念父亲的长篇人物传记博文中,用了很大的篇幅,隆重地将高国新院长的革命事迹,记入了文章之中!希望他的功德和事迹,也能在我的文章中,流芳百世!
言归正传。当年,我父母所选择的婚期应该是并不理想的,他们是在新兴的共和国成立之后所经历的最为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里结的婚。在那个全国人民都是饥饿难耐、童叟皆菜颜的三年时间里,曾经号称为“大胃王”的我父亲,究竟是如何与我的母亲“喜结良缘”和共度难关的?我现在已经无从知晓了!不过,靠着我父亲当年的高工资和我母亲天生的温良恭俭让、贤顺淑德,他们应该是并没有受到过太多饥饿的困苦煎熬。因为,在中原大地饿殍遍野的那个饥荒时期,偎靠着湖北武汉长江洞庭渔米之乡的慷慨厚馈,旧楚地的人民尚能温饱有“鱼”(余)、生活幸福,实属为上天对楚民们的特别怜悯和恩泽。所以,在我小的时候,尤其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父亲一定要在他所拟定的节日菜单上,特别备注要购买回新鲜鱼类和豆腐为节日食材的主要原料,他还美其名曰为这是“年年有鱼(余)、年年有腐(福)”的美好寓意。我想,这大概就是因为他们当年在长江之滨、洞庭之畔所惠泽的“鱼恩”和幸福难忘吧?那个全中国人民都不堪回首的三年,足足的一千零一夜,应该是故事多多!
大约是在我父母结婚一年多之后,老许家里的第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了,这就是我的大哥。我的大哥出生在上世纪1962年苦仄寒冷的冬季里,在那个时候,正是全国人民忍饥挨饿、饥肠辘辘地观看着苏联老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听着剧中人瓦西里说着那句“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台词,极度憧憬着粮食丰收、不再饿肚子而望梅止渴的深冬季节里。
尽管彼时仍在全国性饥荒灾祸的最艰难时期,但许家大公子的降诞临世,无疑还是给我的父母亲大人和我母亲的娘家里的亲人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因为,在我母亲娘家人里,我的大哥是第一个出世的第三代长外孙,我的外婆对于这个大外孙尤其是欢喜爱溺,她一直是把我大哥的降临诞生提高了一个妇人之见的层面,看做是刘氏家族里第三代子孙们的“引路人”!她还非常固执地认为,正是由于我哥哥的出现,才会有了后来的那十七个姑表堂兄弟姐妹们的继往开来!可惜的是,由于我的大哥也是老许家里的第一个孩子,我的父母并不情愿去让老人家来盘带,所以我的外公外婆当时并没能够“有幸”亲缠躬喂,只能是远在湘水之滨的长沙城里望江兴叹了!
当时,我那浑身充满音乐细胞和艺术气息,且习惯于喝着俄罗斯格瓦斯汽水、吃黑列巴面包和俄式大红肠的父亲,用了一个非常洋式的音乐曲牌名来为他的长子取名字,他给大儿子取了一个十分别致的名字叫做“尔卡”。这个“尔卡”名字的来历渊源,最早是出自于一种音乐的曲风“波尔卡”,而我父亲截取了这个“波尔卡”后面的尔卡两个字。据说,我父亲老家的那一辈人们,都是必须按照许家的家谱来排序取名的,如我父亲的那辈人,他们名字中间所范的字为“振”字,即为许家的“振”字辈。到了他们的下一代人,则应该是范为“世”字辈了。所以,我东北老家的那些堂哥堂姐们,都是叫做世英、世伟什么的,据说这个辈分还与解放军里的那位著名虎将许世友先生为同宗同辈呢(不过,我们东北老许家与这位解放军将军之间,并无无血脉牵连,至多算是五百年前的一家人而已!我并不想因此与之沾亲带故、沽名钓誉)!若当初我的父亲也是按照这个祖上传下来的老规矩来给他的儿子取名字的话,那我哥哥的这个洋名字可能就取不成了。幸好,我的父亲特立独行又是天性叛逆,且还是那种头枕反骨的倔强脾气,他才不管不顾他那些老家里的陈规旧格呢!说来也是,在这个时候,我父亲的高堂、长戚和亲人们,还都远在冰天雪地的北国吉林梅河口,且他因为早年间的那一次逃婚远足、不辞而别,一直是心存愧疚和不敢面对的!在长达好几十年的时间里,他一直都不敢与家里人联系,所以也乐得是没人约束,所以那些东北老家里的老规矩,就被他给省略免掉了。
曾经听一些老辈子人告诉过我说,当年我的父亲非常宠溺我的那个大哥,甚至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据说我父亲常常会把他心爱的大儿子架在自己的脖子上“骑大马”,也叫做是“骑梗梗”。而我那尚在幼年时代的大哥,常常会顺势就在父亲的脖子上撒野流尿了!这样的情况,往往还会引起父亲同事们的大呼小叫和困惑不解:“许老师,你儿子又在你的脖子上拉尿了,你怎么一点也不在乎”?在这个时候,我的父亲总是会表现出一脸满不在乎的表情:“这是小孩子拉的尿嘛,有什么好大惊小怪什么呢?一会儿擦干净就是了”。像这样的境况,好像一直持续了好几年,直到后来我的降临和弟弟的出世之后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那可能是因为我父亲的儿子多了,他这个做老爹的已经开始不稀罕了的原因造成的吧?老话曾说:皇帝爱长子,百姓喜幺儿!但在我父亲的心里,却正好相反。
其实,在我哥哥五岁之前的那些美好日子里,我父亲过得还是算很惬意的!当时,年轻有为、意气风发的他,如愿以偿地娶回了漂亮温顺的湘妹子为妻,又给他生下了一个人见人爱的大胖儿子,且他舒适的工作与兴趣盎然的业余生活又过得是如鱼饮水,根本就看不出未来还会有什么苦闷烦心事儿会来困扰着他!这个时候的我父亲,就像是一首老歌里的歌词儿所唱的那样:“阿里,阿里巴巴,阿里‘爸爸’是个快乐的青年”!
然而,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我的父母十分艰难地共同扛受捱过了那几次的“左右”难择和温饱难得的人生风浪之后,又一场根本不可能逃躲掉了的命运劫难,就像一头躲在黑暗之处的掠食猛兽,正在不远处的地方,瞪着一双莹绿幽幽的兽眼,悄然无息地静候着他们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