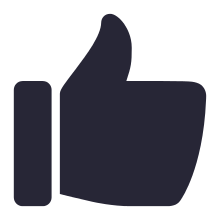我母亲最初在渡口工作了差不多有六年左右的时间,而在这六年时间里,以她一位名牌医大高材生毕业的资历和能力,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任用、利用和发挥!因为,在新兴城市里的医疗卫生条件实在是太差了!当地的医用器械、医疗用品药品以及医疗手段的严重贫乏与匮乏,使我母亲的满腹经纶竟毫无用武之地!她就算是用足了她的洪荒之力,恐怕也是无能为力的!这期间,她曾因工作需要而带着我短期远援于大凉山彝族自治区的老少边穷地区去当了一位“赤脚医生”。我还依稀记得当初她带着听诊器、肩背着那印有红十字标志的牛皮药箱,奔走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山头田间,为彝族同胞们诊病治疗还有接生时的情景。我一直在想,当身为医学专家的我母亲,在背起小药箱,行走在田梗、草房还有那些偏僻的小山村时,她的落寞、落差之感究竟会是怎样子的?有一点我敢肯定,我母亲是绝不会心甘情愿的!记得她曾在一次观看印度电影后对我说过,在国外医生好吃香!会打个针都可以赚那么钱!如果她能在国外行医的话,以她的医术与医德一定会收入不菲!可惜,她没有这样的好命。但她认命、屈从,从不违和,这也是母亲性格中那“逆来顺受”的秉性使然。在我长大以后,从她对待我父亲的态度上,我看得更为直接和清楚!
母亲和父亲带着我们生活在大山沟沟里的最初几年里,虽然当时当地的生活条件艰苦,但我们家的生活也还算是富足、平稳和平静的。因为他俩高超的医术和对待病人如亲人的态度,赢得了大多数人的信赖和尊敬,这也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的好处与益处以及实惠。在当年三线地区生活物资严重贫乏的时候,被我父母医治好的司机朋友们,经常会从远方跑长途运输回来时,带给我家一些油面米肉菜糖乳等亟需和短缺的紧俏商品,甚至还会帮我家买来许多市面上根本无法见到的鹰牌炼奶和上海产梅林牌午餐肉罐头还有极为少见的上海大白兔奶糖等等稀罕物品。记得在家里这些物品囤积最多的时候,竟然是用一个大汽油桶来盛装午餐肉罐头的!这在当时每人每月仅有几两肉食肉票定额定量供应副食品的艰苦年代,是不可以想象的。不过,这些难得的食品,并没有让我那任性顽皮的大哥所珍惜,他甚至还曾用过两听珍贵稀罕的午餐肉去与小朋友们换回来了几张脏兮兮的旧烟盒!不知当时用烟盒换回午餐肉罐头的小朋友回家后会受到他的父母怎样的奖赏?但我哥哥当时肯定是非常得意的!他只喜欢玩,完全是不计后果地玩(这也是他的命)。用几听罐头去换回了“好看”的烟纸,是他认为“划算”的好买卖。好在家里罐头数量太多,少上个几听,是根本看不出来的!他也绝不会因为几听早已吃腻了的肉罐头而心疼的!
我的父母,带着我们三个顽皮捣蛋的小男孩,在那荒凉的山沟沟度过了几年相对平静的生活,算是暂时避开了那场惨烈的文攻武卫、斗私批修和破四旧的文化革命运动的风口浪尖。他们并没有因为那场运动而受到什么非人的遭遇,也没有蹲过牛棚和挨过批斗。不过,我父母那一脑门子里的医术却也因此无从施展而被埋没了。他们在以精英和专家的身份来到这个完全没有医疗基础的穷山沟沟时,始终得不到正确或是正常的任用与重视。他们俩是同时被下放到基层施工单位里条件简陋的医疗队当了普通卫生员的,而且一待就是好几年。不过,他们在与那些普通工人们打交道中,结识了许多朴实的好朋友。那时,若我家里有任何需要时,都会有人前来帮助他们,且不辞劳苦不计报酬。家里的所有所须的木料会有人及时运来,还会有人心甘情愿地为我家里免费手工打制各种家俬家具。这期间,我的家里几乎什么都不缺,比起当时的许多家庭来说,我的家无疑是幸运的。对这样的生活状态,我的父亲母亲应该还算是满意的,在当时那样的大环境中,他们能有这样衣食无忧,受人尊敬的生活,也是难能可贵的。然而,这种“小富即安”的平静、平常的生活,又一次被打破了!而这一次打破的平静,竟然还是一个对我父母似乎是好的消息带来的。
大约是在他们“扎根”这个位于山区的三线城市的数年之后,我母亲终于等来了一个是她祈盼已久的一个契机、一个大好的消息!可能是因为我与母亲长得最相像,或是因为母子连心的缘故,我甚至到现在还能感受到当时我母亲是何等的欣喜若狂!那是因为在上世纪的七零年代初期,日本援建了位于湖北省武汉市的武汉钢铁厂一个冷轧钢板的工业项目。因这种钢板规格的原因,这个项目被称为是武钢的“一米七工程”。当时这个项目的实施,需要从我父母所在冶金建设单位中,抽调一部分人马前往我父母当初的老单位武钢支援建设。所以,这个有可能再回到原来工作过的地方的好消息让我父母(当然,特别是我的母亲)尤感欣喜!因为,武汉离母亲的老家湖南长沙很近,她太思念她的亲人们了!不仅如此,当时正在武汉工作生活的,还有母亲的亲大姐!估计这样的好消息,曾让我的母亲彻夜难眠。但是,由于是支援建设,主要派去武汉支援的工种人员都是建设队伍,随行医疗队的名额十分有限。不知他们当初是用了什么办法,最终上面的领导是同意了由我母亲一个人带着医疗小分队随支援建设的大部队前往武汉工作。这样一来,从结婚开始就从未分开生活过的我父母,注定要过相隔数千里的两地分居生活了。我那特别体恤母亲的父亲,虽然支持母亲远赴武汉工作,却也不得不落寂地带着正值顽皮之年的两个儿子生活在原地了,按他的原话说,我们当时正值“七岁八岁讨狗嫌”的年纪,特别不好带。在这三个孩子中,母亲最后是选择了带我一起前往武汉工作,这可能也是因为她最喜欢我、最宠爱我的原因吧。
时隔多年,我仍清楚地回忆得起当年我随母亲坐火车前往武汉时的情景。母亲在与我父亲和大小两个儿子依依惜别之后,惺惺离开了渡口这个山沟沟。她在火车上显得十分兴奋,平常时不太多言语的她,一路上竟不停地给我讲述着车窗外的风景。记得那一天正好是那一年的新年元旦,整列火车都沉浸在新年新生活新纪元开始的欢乐之中!而这马上就要开始的新生活,因距离母亲的期望值更为接近而挑动起了她快乐的源泉,她的话匣也由此被打开了。我还记得她说列车掠过的一座大山,像是一座象鼻子山(后来我才知道,那象鼻子山根本不在这车窗外,而是远在广西桂林),山下还有田有水,水里有鱼有青蛙有藕还有黄鳝等等。这些由母亲描述的一切,小小年纪的我是完全听不懂的,直到我随母亲在武汉生活了好几年之后,我才弄明白,那些东东都是生长在旧楚国地域湖南湖北的!而我母亲跟我讲这些,可能是因为她实在是太想家了!似乎车窗外的那一切,都是与她的家乡是一模一样的。
那一次随母亲到武汉,是我记事之后的第一次出川旅行,也是我第一次坐上火车!我对车窗外面的一切都倍感新鲜!还有更为新鲜的,是在这列载着我和母亲的火车途经长沙火车站,做短暂停留时,母亲在长沙的弟妹们几乎都到火车站来探望她和我了!那个场面时至今日我仍然记忆深刻!母亲当时好高兴好激动!她的七妹八妹更是拉着姐姐的手,不停地在原地跳啊跳的,脸上都笑得堆成了一朵花儿!那也是我懂事后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舅舅姨妈们,我害羞地拉着妈妈的衣角,怯怯地躲在她的身后。可那些“陌生的”舅舅姨妈们也不放过我,一个劲儿地对我又抱又亲的,简直是把我吓坏了!而当时满满一列车我母亲的同事们,都被这样浓浓的亲情所感染,估计他们也是特别羡慕我母亲吧!
母亲和我到达武汉后,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了妈妈的大姐一家。记得那时候,妈妈只要是有空和有和顺路车的活(那时我们住的地方还没有公交车),她就会急急忙忙地跑到单位食堂里买上许多的馒头花卷包子还有肉菜米面和油等食品,坐上单位的顺风车,到距她工作的武钢厂前(地名)并不算太远的红钢城、八大家(地名)去探望她的姐姐姐夫一家。这期间,我还曾随母亲坐火车回过好几次她的家乡湖南长沙,这也是在我懂事之后,第一次见到了我的外公外婆!妈妈让我用长沙人的土语土话,称外公为“嗲嗲”,叫外婆“娭毑”。记得我母亲在她自己家里时,那个快乐、那个舒畅还有那个亲情喷发,我也是至今难以忘怀的。
母亲最初在武钢工作的那几年里,一切还算顺利,她以她那高超的医术以及高尚的医德加上她那颗医者仁心,受到了伤病员以及单位领导、同事们的交口称赞。她在她的行医过程中,是没有节假日和休息时间的。我经常会在睡梦中被人用急促的敲门声中吵醒,我也是早已习惯了母亲这样在深更半夜被人找去出诊的情况。这样的深夜出诊,是妈妈的家常便饭,而且是没有额外的报酬的,甚至连加班费和夜宵也是没有的。可我的母亲,却从无怨言,在她眼里,这是她义不容辞的天职,病人与病情永远是第一位的,也是高于一切的!她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诚心诚意服务于患者的白衣天使,任劳任怨,再苦再累也在所不辞。我无法统计在妈妈的一生中,曾救治过多少位患者病人的生命,也不知道曾有多少婴儿是经她的手才呱呱坠地的!但我知道,妈妈的一生,从未私下里接受过伤病员的任何红包和物品!她的医德相比今天的某些医者,要崇高和伟大得多得多!不知能有多少今日的庸医和缺德医者,会在她的灵前汗颜失色?这样的白衣天使,难道不算是普渡众生的观音菩萨下凡再世吗?在我的印象中,能无私做到这一切的医生,惟有我的妈妈,再无旁类!
在武汉时,虽然妈妈暂时与我的父亲和两个幼子间两地分居着、情感煎熬着,但她还是获得了另一种亲情的补偿,加之她以饱满的热情,辛勤工作在治病救人的崇高岗位上,日子过得也还算是舒心和顺心的。这期间,我父亲还曾带着我大哥和三弟前来探亲,甚至父亲还曾随单位上的文艺宣传队前来武汉慰问演出,这也给这对暂居两地的苦命鸳鸯提供了短暂而宝贵的欢聚时光。还有一个特别令人振奋的好消息是,父亲也在单位上积极活动之中,希望组织上照顾,他也能前来武汉工作,能与母亲和孩子结束两地分居的相思之苦。这样的可能性后来变得越来越大,似乎已经唾手可得……
母亲在武汉工作的期间,也遇到了让她最伤心难过的一件事情。那是有一天,她突然接到了长沙发来的噩耗电报,她那曾身为中国早期民族资本家、实业家的父亲,因积劳成疾、囤郁致病而罹患癌症,不幸过世了!而那时的外公,还不到六十岁,正值盛年!母亲在前往家乡为她至爱的父亲奔丧戴孝时,我也随她一同前往了长沙。记忆中,那一次母亲在长沙家里待了很长的时间,这是因为她的责任重大。她既要抚慰她那伤心欲绝的母亲,还要安抚她那些年纪并不太大的弟妹们,同时还得强忍着悲痛与悲伤!这期间,我母亲的所作所为,让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是孝心与孝顺?也让我深刻感知到了亲情的力量与重要性!而这一切,对于我的一生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后来,妈妈一直在家里的案头上摆放着一张有外公照片的“职工公交月票”,还有一盘花生米。她告诉我,外公最喜欢吃花生米了,而外公太节约,连霉变的花生米都舍不得扔掉,可发霉的花生米有致癌物质黄曲霉菌,这可能就是我外公罹患癌症的主因。可是,我真的感到悲哀,一代民族资本家的富豪,竟然因为花生米断送了生命。若是他仍然是烟厂老板的话,这样的事情应该是不可能发生的。可惜我的外公那么年轻、那么有才华、那么有实力、那么有头脑、那么有知识,却没想到让这小小的花生米作了祟!
然而,人生总是在坎坎坷坷之中悄然度过的,从来也不会一帆风顺,这对于我家,尤其是对于我母亲而言就更是如此!当我的父母正筹划着尽快举家回迁武汉工作的紧要关头,我的家里又突遇了一件突发的大事件,生生打乱了他们的这个计划,也彻底摧毁了他们的如意小算盘。
先是我父亲在渡口坐大巴车去演出时,因山区道路颠簸而导致膝盖关节处的半月板撕裂骨折!而他又因身患高血压冠心病而突发了一次严重的心肌梗塞,差点儿致命!幸亏父亲也是一位医道高深的医者,他紧急自救,加上我家就住在医院大院里,在危急时刻他被抢救过来,保住了性命!当得到丈夫病危的消息,急急忙忙地从武汉千里迢迢赶回渡口的我母亲到达医院时,我父亲的病情依然十分严重,时刻都有生命危险!好在后来有我那同样是医学专家的母亲在我父亲的病床前专业侍候和调理下,我父亲终于躲过了他生命中的一劫,转危为安了!医院的领导们将这一切是看在眼里,也记到了心里。他们深知我母亲医术的重要性,以及他们太缺乏如我母亲一般,医术高超的医生了!于是,他们以我父亲身体状况为由,动员我母亲尽快调回到渡口来工作,以便照料我那刚刚大病初愈的父亲和几个无人照料的孩子!母亲权衡良久,面对这样的现实,最后不得不妥协了。无奈之下,她只得又重新回到暂别三年的渡口工作了。而她这样做的代价,是她必须再一次远离了她的故土和亲人,还有最终将她宝贵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那个并不是她故乡的大山沟沟里,这是后话。
母亲带着我们重回渡口之后,又重新恢复了他们过去所过的同样生活。只是,由于母亲的医术与医德,她被组织上调至单位的职工医院里工作,不再是被下放到基层单位去当一个小卫生员那么委屈了。这一是单位的需要和领导们的关照,二是为了让她方便照顾我那刚刚大病初愈的父亲。
当母亲到单位上的职工医院报到后,我们家终于分配到了一套面积不算太大的两室一厅的楼房居住,后来还曾搬过一次家,住进了新楼。从这时起,他们的生活才勉强算是走上了正轨,像个真正的家了。这一年,距我母亲从世界医学名校同济医科大学以高材生毕业已整整过去了二十年,二十年啊!试问,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而这最黄金、最宝贵的二十年,我母亲又是怎样度过的呢!她真是错生了一个时代,令人惋惜唏嘘!
在我母亲以专家的技术和身份来到她的新岗位职工医院工作时,她又受到了明显不公正的待遇。这位名牌医科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她在这里所能获得的职务职称仅仅是一名“住院总”医师而已。可能不是当医生的朋友,并不一定能知道这住院总医师是个什么样的职称?我其实也不是很清楚的,只知道这个职称连主治大夫都不是!而主治大夫也仅仅只是相当于学院里的讲师级别!那么,这样算下来,住院总医师应该只能算是医院里最低级别的普通岗位的医生,大不了能相当于学院里的助教级别。可我那温顺的母亲竟然并不去与人争辩!她曾在大学毕业后就担任过武钢医学院的讲师和班主任,又曾在一线的医疗岗位上默默奉献了二十年的宝贵青春!但这一切都没有为她的职称晋升带来过一丝一点儿的益处。她依然拿着那特别微薄的工资,与年轻一代的青年医生们一样三班倒地值班,辛苦地工作在医务工作者的第一线。
在这段时间里,母亲在我父亲身体好转后,曾带着我们几个儿子一起,回到过长沙老家去探望她的母亲和她的弟妹们(甚至,她还曾带着我们不辞辛劳,连续坐上三十多个小时的长途列车,回到了我父亲的故乡,代替他去看望他故乡的亲人们)。她在家乡长沙,受到了她母亲和她的弟妹们的热情款待。她的每一个弟弟妹妹都争相邀请她到自己家吃饭和小住,还有一些经济上并不是太宽裕的弟妹们,总是硬给她塞钱塞物,生怕怠慢了这个和蔼可亲的二姐!记得我们准备坐火车离开长沙时,我那在工厂里打零工挣钱的小舅舅前来送行,他大概先前已经塞给我妈妈一些钱就与我们告别了。可是,当我们在候车室里等着上车时,他竟然又跑了回来,他努力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找到了我们,再次塞给他二姐五十元钱!妈妈极力推托着,却也是无用的!因为小舅舅塞完钱给她,就连忙转身跑掉了,追也追不上!这样的亲情,着实让人感动不已!而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例如我那从国外留学回来的著名学者的舅舅,也是将他在国外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钱,夹在他的书本里,一但他见到我母亲时,就会从书本里翻出来几张花花绿绿的外币或人民币现钞塞给我的妈妈,他还曾将他在国外穿过的好衣服,一古脑都打包寄来给我们三兄弟穿!当然,还有我亲爱的的大姨、三姨、七姨、八姨,大舅、立舅、满舅、毛舅、小舅以及所有的姨爹、舅妈等等,他们在资助我妈妈时,都是从不吝啬、从不心疼和从不自私的,他们总是会大方地慷慨解囊,这样的亲举,曾让我的母亲深深感动!这样的亲情和浓浓的爱,也让我永志不忘!相信我母亲最快乐、最温馨的时候,也是在她与这些亲人们欢聚一堂的时刻!在此,我特别代表我的母亲感谢每一位亲爱的舅舅、舅妈,姨妈、姨爹们!希望你们都健康长寿,幸福如意!相信,这也是我母亲最希望看到的,在她的心中,她的所有亲人都是与她息息相通,血脉相连的!亲人们的快乐、幸福和健康,就是她最大的愿望!
记得当初我母亲带着我们几兄弟回到东北时,她同样也受到我父亲家人的热烈欢迎和高规格礼遇!她是在我东北老家里面,第一个可以上炕与老爷们一起吃饭的女性!这在我那东北故乡的陋规森严中,是绝无仅有的!因为,我父亲的家乡人,把我母亲当成贵戚(东北话,尊贵亲戚的意思)和贵宾来接待的!他们也非常敬重这位美丽善良贤慧以及和蔼可亲的南方媳妇儿。因此才破例打破了家规家训(东北人认老理儿,轻易是不敢破了祖训家规的),以此来表示他们对我母亲的态度。这期间,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往事,那是身为许家二少爷媳妇的我母亲,竟然还带着礼物和她的孩子们去探望了一次那位在几十年前因我父亲的逃婚与逃跑而入了许家门又未真嫁的封建包办婚姻的受害女人!而在东北那旮旯,这种入了别家门儿又被抛弃的女人,是再也难嫁出去了的!那个可怜的女人,在我父亲逃婚之后,也是终身未再嫁了。不过,当我母亲带着我们登门拜访时,她竟然完全没有了怨意,她一个劲儿地夸赞我母亲漂亮和儿子们乖巧,还与我母亲成了朋友!奇怪吧?其间,那个可怜的女人还仔细地询问了我父亲的所有情况,显得极为关心,估计她真的是爱着我父亲的吧。但我看得更清楚的是,我母亲那颗仁爱、善良和大方、大度的心!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没想到我母亲的这颗医者仁心,竟也是能包天容地的。
可惜的是,我一直没有在家里和舅舅姨妈那里找到或看到一张刘氏姐弟们十全十美的全家福,真是令人遗憾!后来看见姨妈在群里说,当初没有照全家福的原因,是我外婆没让大家去照相馆照,按她老人家的理论,是“越缺越圆”。不知道外婆的这个“理儿”是否是真有道理?不过,在我母亲早早离世之后,我的这些娘舅亲人们,一直都健康无虞!就算是身染沉疴,最后也会安然无恙!似乎真的有神灵暗中相助。这或许真的是我外婆的“理论”奏效了吧?若果真如此,那一定是我妈妈心甘情愿地为她那些至爱姐弟们贴补了阳寿,护佑了他们的平安!我深信。
母亲重回攀枝花工作几年之后,身为医术高超的“内外妇儿科”的专家级医师,我母亲竟然在她四十多岁时改了专业去放射科当了医师,这真是有些不可思议!而母亲的这次改行,竟然还是因为她思乡心切!以至于才忍痛放弃了她行医多年的本职专业。
当时,母亲所供职的医院要创办X光放射医科。这个科室的创办,在当时落后的三线城市里的职工医院是一个崭新课题,医院引进的X光放射投照影医疗诊断设备无人能用会用,而且因为X射线对人体有严重伤害,会造成从业者的职业病,一般人都不愿意从事这种工种,可以说是避而远之,讳莫如深。不过,当我的母亲听说,进入放射科的工作的医生,将有机会前往位于长沙的“湘雅医学院”进修两年时,她竟没有与我父亲商量一下就毫不犹豫地报名了!此时我父亲的身体已经有所好转,表面看起来并无大碍。母亲希望借此次回长沙进修的机会,能多去陪伴一下年事已高的老母亲以及她日思夜想的弟弟妹妹们!这个计划自然也被我父亲所支持,母亲的回乡学习也成行了!
记得妈妈在临行前,一直张罗着给家乡亲人们买礼物。然而,地处穷乡僻壤的钢城攀枝花,实在是难有拿得出手的好礼物能带回去送给亲友们。她最后大概是捎带了许多攀枝花特产的铁制品去了长沙。我那个著名作家的大舅舅,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长沙晚报》上,讲述我母亲带给他的那口攀枝花特产的生铁小锅!他的家里一直到前年仍在使用中,一共用了三十多年才用坏的。每每当我们到长沙的大舅家里做客,他都不忘把这段往事翻出来讲给我们几兄弟们听,那是他对二姐的浓情厚意,让人感动和感慨不已!但我现在实在是想象不出,当初我母亲一个人回家乡时,是如何带回去的这么多、这么重的“铁疙瘩”?要知道,她当初从攀枝花市坐火车到长沙,必须要经过云南昆明下车,再中转换乘另一辆列车之后,才能到家的。以我母亲那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又是如何应对这样的难题的?想必只能是亲情的力量感召,让她徒添了洪荒之力,最终将这些铁器带给了她的亲人,也使她的亲人们更深刻地记住了她!
(未完待续)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