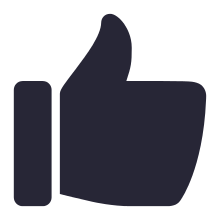其实,我对于父亲前半生经历的那些认识和了解,只是断断续续知道的故事碎片拼接而成。有一些内容是努力回忆在我的童年时代,父亲曾经絮絮叨叨地念给我听的往事,有些是亲戚朋友们闲聊时讲给我听的,还有一些就是我小时候偷偷看过的父亲本人在特殊年代时,写下的几大叠秘不示人的交待材料中才得知的。当然,我父亲后半生中的那些经历,许多都是我与他老人家共同生活时,真实发生过的故事,有待我在后续的文章《父亲的后半生》中,再慢慢地讲给大家听。然而,正是这些漂浮在父亲往事中的那些故事碎片,才组成了我对父亲的完整认识。本次的长篇博客连载内容,其实就是我写下的一篇有关父亲记忆的亲情流水账,希望朋友们能有耐心读下去。
我在前面说过,我父亲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他生于上世纪前叶1929年的旧历7月,属相是蛇,但他未对我说过他属蛇,而是从来都说他属的是小龙。由此可见,父亲是一个很守礼教传统的人,他极认祖传的那些个老理儿,客观上就是一个很保守的旧时代文化人。不过,以他当年断然冲破了封建礼教,蛇往龙形地开创了他新的人生之路而言,他又是一个自由散漫、思想进步和极有主见的新时代文化人!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评价,很难契合为同一个人身上,而我父亲却真正地做到了!那他到底是一尾蛇还是一条龙呢?朋友们看完我的这篇纪念父亲的文章,也许自会有明断的。
言归正传。其实,从我父亲那一代人之前的一两代人开始,他们已经不能再算是山东籍的闯关东鲁民,而是真正的东北人了。不过,我并不知道我父亲应该算是闯关东的第几代山东***?因为,我不清楚我的祖上究竟是在什么年代从山东***到黑土地东北吉林的?从现存的有关山东客闯关东的资料上显示,鲁民们开始闯关东的时间,最早可以上溯到公元1644年至1667年的这二十三年间,那段时间的山东鲁民们不顾大清朝的严格禁令,冒死从陆路闯关(山海关)以及从渤海水路北上闯关东的人数为最多。历史上真实的闯关东,那可是真正是“闯”的!由于满清王朝在入关主政之前,满人们的旧京故土就在那片广袤无垠的黑土地上,所以大清国当年颁下的铁律,是绝不允许汉人们出关为民的。所以,自清军入关之后,满清朝廷就派重兵把守着北上必经之路山海关,对那些敢于擅自闯关的汉民们,采取了非常残暴的武力镇压政策。因此,那些因为贫困、饥荒或生活所迫而选择北上谋生的闯关汉民们,境遇是十分危险的,他们的闯关之路艰险重重,往往是九死一生,十分惨烈。在闯关路上如此的险象之下,许多闯关东的汉民开始选择了从渤海的水路北上,以求避开凶悍的八旗清军,这也是当年“闯”关东的一种方式。不过,渤海湾上的大清水师也不是吃干饭的,他们船坚炮利,曾经是远强于倭船的海上霸主。所以,闯关东的陆路实属不易,海路亦非安道!不知曾有多少的中原水客在渤海湾葬身鱼腹?我并不清楚我的祖先,是否就是在这段时间里,经由渤海水路到达了辽宁营口港的?现如今又在许多老辈子人已经过世了之后,我就更不可能再清楚地知道这些太为远早的历史了。如此说来,我父亲至少也是闯关东数代人之后的山东***了。做为山东闯客后代的我父亲,无疑是非常幸运的!在他的童年生活中没有境遇闯荡之苦,也没有受到过偷渡客般的惊恐与惊吓。他是在一个富裕的大户地主家庭里诞生和长大的一个纨绔子弟少爷公子哥。在父亲生活的那个年代,***东北的老许家那是相当富裕和有钱的,是一个十足的土豪家庭。据我的一位叔伯告诉我说,当年我父亲的奶奶过世时,光是用在陪葬的枕头里,就放入了八斤多重的护枕黄金,有些居然还是大块大块的天然狗头金块呢!这还不算其他的陪葬品。我想,祖奶奶如此的墓葬规模,已经足以引起那些摸金校尉们的鬼吹灯了!所以,当年我回到东北老家探亲的时候,曾有一位堂亲郑重地与我商量,说要给曾祖爷爷奶奶起坟重葬,以免被那些盗墓贼们占了大便宜。但是,他的这个提议,被我坚决地否定了!因为,父亲在世时曾经对我这样说过,祖坟就是我们的祖根儿,那是绝对不能亵渎的。不过,老许家当年算不算是一户真正的土豪,由此可见一斑吧?
其实,老许家曾祖辈们儿的那些历史,我知道的也并不太多。但是,我对我的亲爷爷亲奶奶还是有所了解的。在我的兄弟们当中,我是唯一一个亲眼看见过他们的亲孙子,这是后话。虽然,我的一生中也只是见过他们一次而已,但记忆深刻。据我所知,我的爷爷因为是出身于富豪地主的家庭里公子哥,所以他从小就受到了极其良好的私塾教育,很有文化,他的文章和书法在当地都很有名气。因此,我爷爷长大成人之后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当地的教育部门里担任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学究,专门负责巡视当地所有学校的教师和教育工作。可能是因为家庭的原因,我的爷爷居然还很奇葩地迎娶了一位俄罗斯女子为妻(不过,还有另一种说法,说我的奶奶是满清八旗中的正黄旗人家里的格格,但我却并不以为然。因为,在那个满清王朝统治天下的年代里,即便是出身于富豪家庭的汉民我爷爷,恐怕也是娶不到根儿红苗正的皇亲国戚、八旗子弟的格格)!在我的记忆中,奶奶长得很白净(不太像是黄种人),但她具体的形象我现在已经记不太清楚了!所以 ,她是不是一位外国的女子,我现在无法再真切地回忆起来了。不过,我那有着二分之一混血血统的父亲(若果真如此的话),长得是非常洋气的,他生就得浓眉大眼,面部轮廓凹凸有致,十分帅气,还有着一甩的自然卷大波浪头(这个自然卷头,后来还遗传给了我),很有俄罗斯人的范儿,甚至包括只有着四分之一俄国血统的我和兄弟们,都经常会被朋友们认为是很典型的混血儿。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和很关键的佐证是,当年我曾经只身前往首都北京,去报考中央民族学院的音乐舞蹈系表演专业,须要在报名时提交一份少数民族的身份证明,而我的户口上却明明白白标注着汉族两个字。为此,我的父亲还亲自去找了我户口所在地的当地派出所,竟然给我开出了一张纸质盖章的公安局户籍证明公函,那上面清清楚楚地证明着我是一个“俄罗斯族”。不论这个猜测虚实真假,由此可见,我奶奶的身份的确是有些来历的。而这样的情况,从侧面也可以这样理解一下,当年老许家在东北那噶哒,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户富可敌乡的富裕人家了。因为,在当时那个等级分明的旧社会年代里,我奶奶无论是俄罗斯人的女子或者是满清旗人家里的格格,都不太可能会下嫁给一个汉民穷小子的!我想,我的奶奶绝对算得上是那种宁可在宝殿中哭,也不会在马车上笑的小主儿!然而,不管我奶奶当年是哭还是笑,她最终还是嫁给了老许家当汉人家的儿媳。自此伊始,许家后代们的基因得以有效地改变与强化,竟然还有了异族人的血统。但这一切都不重要,最为关键的是,自从有了我的奶奶之后,才会有了我的父亲,也才有了我和我的兄弟们!这才是环环相扣关键的关键,若差之毫厘,必将谬之千里!
我父亲的童年,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东北大家庭里的公子,他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被家乡人尊称为许家二少爷或者二爷。我父亲跟我爷爷一样,也是从小就受到了十分良好的私塾教育,文化修养很高。我父亲有过一个兄长、两个弟弟,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家里一共是兄妹五人。不过,我只见过父亲的兄弟们和姐姐,却没有福份见到父亲的那个我应该叫做小姑姑的妹妹。因为,我的这位小姑姑在她还很小的时候,就因为罹患了疾病而过早夭折了。当年,正是因为小姑姑的因病夭折,才促使我的父亲后来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弃艺从医,最终成为了一位身穿白大褂的职业医生,这又成为了他结识我那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做医生母亲的最重要原因,这也是他们俩人因为志同道合、两情相悦而结合,后来才生下了我们三兄弟的真正契机所在。这可能就是冥冥之中的上苍安排吧?我很庆幸,我们几兄弟都应该感谢我的这位从未谋面过的小姑姑!可以说,没有小姑姑的那段悲伤往事,也就不可能有我们今天的存在了。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据父亲说,当年的梅河老许家一直都是阳盛阴衰的,家里面的男丁总是多过于女性。所以,我父亲一向都特别疼爱他的姐姐、我的大姑姑,以至于在大姑姑后来病故之后,我的母亲一直都费力地隐瞒着我的父亲真相,不敢把这个噩耗告诉他。不过,我从父亲的只字片语中了解到,我父亲心里其实是最喜爱他的那位小妹妹的。不幸的是,我的这个小姑姑在尚不到髫年的五、六岁小小年纪时,竟然得了一种在当时几乎是不治之症的白喉病。我的父亲为了救活他心爱的小妹妹,还曾经用一个大铁饭盒装满了银钞,上面还盖着一层汤汤水水的饭菜伪装好,就像样板戏《红灯记》中的那个地下党李玉和保护密电码一样,将那一饭盒救命的钱款伪装好,然后穿着一身学生装赶着区间通勤小火车,来到海龙县城里的教堂,去找洋传教士医生购买医治白喉的特效药~青霉素针药。在那个年代的中国东北境内,除了有满街的日本侵略者,还有无数的伪满军警,更有多如牛毛的散兵游勇、流氓地痞和土匪绺子,可谓是危险重重!我的爷爷之所以会让我父亲这样的一个半大小孩子,抱着那么多的现钞现银,孤身只影就前往了那险象环生的县城里去求医买药,可谓是极为大胆的无奈之举,这可能就是所谓的灯下黑吧!事实上,我父亲在求医买药的路途上未费周章,他非常顺利地赶到了存放着救命灵丹的洋教堂。可惜的是,接待当时还只是一个少年学生我父亲的那位认真、古板和执拗的洋传教士大夫,却因为他手上的青霉素针剂已经过期又没有其他新药为理由,断然拒绝了我父亲带去买药的真金白银和钞票!现在想起来,那位洋大夫真的可以算是一个认真负责的好大夫,他的职业操守可谓一流,并不同与那些见钱眼开的俗医药商。然而,正是由于他的固执,最终导致了我的小姑姑在他哥哥、我父亲眼睁睁的注视之下,因为无药可医而不治身亡了!我父亲说,当时,他那已经处在弥留之际的小妹妹,临死之前是非常清醒和明白的,她甚至还在临终前提出了要穿花衣服和绣花鞋入殓的要求,并在得到了家长们肯定的答复之后才溘然长逝的。正是因为这件曾经令我父亲伤心欲绝的悲伤往事所促,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从那时起就埋下了立志从医,将来能够治病救人、不再让小妹妹那样的悲惨遭遇重演的远大志向。在若干年之后,我父亲的这个理想,在他曲曲折折的人生境遇中,竟然真的得以真正实现了,他***的职业就是一名医生而不是一个艺术家。后来,我曾听父亲跟我说过,当初假如那个洋大夫能将那一盒虽然已经过期但仍有药力的青霉素针剂卖给了他的话,我的小姑姑也许就不会死去了,起码也能算是死马当成活马医吧?然而,由于那个洋医生恪尽医生的职业操守,所以并没有什么“假如”的情况发生,我的父亲只能是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小妹妹撒手人寰了!
由于当初老许家里男多女少,加上小妹妹的早夭,我父亲对于他大姐的疼爱是无以复加的,这也是后话。可能正因为如此,我父亲特别希望能在他的后代中,能有上一两个女儿的降诞。然而,命运弄人,我父亲几乎是“命中注定”此生只能生养三个淘气的儿子而没有女儿,这是他不可违抗的天意,也是他逃脱不掉的人生宿命。
之所以说我父亲命中注定只能有三个儿子而膝下无女,那是有故事的。父亲曾经亲口告诉我一件往事,那还是在他七八岁的时候,正值调皮捣蛋、讨狗嫌弃的少年时期。我的爷爷有一天请来了一位瞎子算命先生到家里来看相,还顺便让这个瞎子算命老先生给正在天井里调皮玩耍中的许二少爷也算上一卦。据说,那个算命老先生起初不知为什么,就是不愿意为我的父亲看相,但他却又执拗不过我爷爷的命令式强迫,只得硬着头皮为我父亲这个只有七八岁大小的刺儿头二少爷相面了。我父亲很清晰地记得,瞎子算命先生在仔细地给他摸骨相面之后,言之凿凿地告诉我的爷爷说,我的父亲将来是不会在东北老家里守着那些祖业生活的,而是会跑到几千公里之外的关外南方去谋生,还会娶回一个小了他八岁的南方女子为妻,甚至还十分肯定地说我父亲一生将只会生养出三个男孩子,一个女儿也没有。据说,当那个瞎子算命老先生说完他的这一番胡言乱语之后,我的爷爷是真的气急败坏了,他不但不给这个瞎子老先生的相面辛苦钱,连照例的招待午餐都不管了,还直接命家里的佣人们,把这可怜的瞎子算命老先生给叉出了许家的大门之外!许家老爷如此的失礼之举,立即引起了邻里邻居和路人们的关注与不解!因为,我那一身迂腐学究气极重的亲爷爷,是非常讲究礼数的文化人,且他历来就是一个好脾气的大善人,又是出身于书香门第、富豪大户人家里的公子哥,他一向都是善待下人、礼让他人的。邻居们起初都不知道,我的爷爷何以会如此大发雷霆,居然将一个可怜的瞎子老先生叉出了老许家的大门之外?这也太不像是许家老爷一惯的处事方式和为人风格了!后来,还是我爷爷亲自在大门口,给众乡亲们讲述了那个瞎子算命老先生的相术种种骗钱“谎言”之后,大家伙儿才明白了这其中的事理儿。简单地跟大家解释一下,在当时的那个特殊时代里,由于交通的不便以及山海关内外的敌对、封索状态,别说是到离家数千里之外的南国了,就是要到数十里开外的海龙县城和仅仅才十几公里远的山城镇上去一遭,那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再者说,许家的二少爷注定是将来继承许氏祖业的传人之一,他的婚姻未来也只能是谨遵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又怎么可能会到遥远和陌生的南方去娶妻生子呢?且还是娶一个小了他八岁的南方女子为妻,连两人相差的岁数都能编得出来!再有就是最不可信的,那个瞎子算命老先生竟然那么武断地算出一个当时只有七八岁还未懂世事的小孩子,将来是生三个儿子、没有女儿的命!这不是忽悠、瞎说和骗钱又会什么呢?于是,大家伙儿一致地谴责了那个可怜的瞎子算命老先生,说他居然敢用如此不着调的虚假谎言来骗人骗钱,甚至还是跑进了许家大院里去行骗,这种卑鄙的行为实在是太可耻了!我是不知道那位瞎子算命老先生当时是如何经受了这样的委屈和尴尬场面的,他可是当地号称为“半仙”的骨灰级算命老师傅啊!我猜想他当时一定是欲哭无泪、满腹冤枉!因为,他当年给我父亲算上的那一卦,后来被事实证明不仅十分精准(仅有我父母之间的岁数之差有小小的差距,不是相差八岁而是七岁零一个月)、且件件得以应验,而且还与我母亲家的一段往事之间,竟然奇迹般神秘地吻合起来了!而我父母家的这两段奇葩的往事,让人不得不叹服,我父亲的一生,是一场早已被上天安排好了的无改宿命!虽然,我的父亲本人并不太相信什么“迷信”,也从来都不是一个宿命论者的拥趸,但这谜一般的惊人巧合,谁又能解释得通呢?实在是太令人费解了。
我在本文开篇时提到过,我曾经在原维基奥秘W网的博客中,写过一篇名为《我的母亲》的长篇博文,在那篇文章里,我还讲到过一件发生在我母亲身上的奇葩往事。在我母亲出生的那一年,是公元的1936年农历八月中旬,她的属相是鼠,跟生于1929年旧历七月中旬的我父亲之间,相差了七岁零一个月,而这个年龄差距与那个给我父亲看相的算命瞎子老先生所言的我母亲比我父亲小了八岁的说法,的确有着小小的差池 。不过,若按照中国人年龄计算中的虚岁习惯的话,说是他们之间是相差了八岁也不为错。在母亲出生的前夕,曾经有一支国军的部队(大约有一个连队、百把人),成整建制地住进了我外公外婆家位于长沙育婴街上的一幢大豪宅里。我在《我的母亲》那篇文章中也提到过,我外公外婆家的那套似若客家围屋般形态的三层楼(还是五层楼?我现在已经记忆不太深了),我在上世纪八零年代中后期的时候,曾经跟随着母亲一起去那里实地探访过。当时,那处古老的大宅院正因长沙的城市建设而处于拆迁施工之中。目测那幢正在被***到一半的百年老宅残垣断壁,真可谓是古香古色、硕大无朋、美轮美奂,绝对算得上是文物级的古宅院!它曾历经过长沙著名的文夕大火,以及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的战火洗礼而毫发无损,还幸运地躲过了建国以后的历次重大运动和文化革命浩劫,连当年“除四旧”这样的毒手都被它成功躲过了,却还是没有能够逃开掉改革开放之后,长沙城市建设的清理和清除,很是遗憾!还好,受到时任湖南省政协***、长沙和平起义功臣、前湖南省的建国后首任省长、原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将军的族弟、我大姨父的父亲程星龄先生的恩泽和特别关照,长沙市政府破例补偿了我外婆家里四万元人民币的拆迁补偿款,这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一笔飞来的横财巨款了,足可以抵值上四个万元户了。不过,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四万块的卖宅款,可真的是一笔可怜到不能再可怜的微薄施舍钱了!因为,像我外公外婆家那样的豪宅若是放在了今天的话,仅仅只是文物的价值就已经是不可估量了,再加上它的占地面积及房屋数量,至少也是市值过亿以上的豪宅!不过,这个问题并不是本文所关注的问题,暂且在此忽略不计吧!我所关注的,是曾经在这幢豪宅里真实发生的另一件奇葩往事,而这件神秘的往事,又与我父亲躲不掉的宿命,以及我和我兄弟三人的神秘来历之间息息相联!这也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谜团,恐怕也永远都解不开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