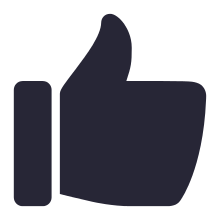安格尔著,朱伯雄译
选自《安格尔论艺术》,辽宁美术出版社,2014年。
一个好的画家只有在熟练掌握自己的业务并真正具备摹写客观对象的本领、最主要的是他学会整体地去构思自己的画面时,即只有当他热情奔放地想一气呵成画完他的画以前,就已胸有成竹,一切才能达到和谐统一。这是作为艺术家所应具有的特色,他得夜以继日地想着自己的艺术。如果你已是一位美术家,就要有这种进取心。一个人从他过去大量的创作实践中可以得出一种经验:即一个有才能的美术家当他个人的能力正好适应他的用武之地时,他每天所创造的却是他以前认为不可能取得的成果。
我觉得我正是这样一种人。我每天都在进步;我从来也不觉得我的劳动是轻松的,而且我的作品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正是相反。我比以前完成得更多,也快得多。面对着我的客观对象我不能不忠诚地画好它。为了挣钱而迅速画完一幅作品,这对我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1813年)。
我想为艺术而永远活下去。我希望让岁月和智慧来纯洁我的情趣,不使热情熄灭。我向来崇拜拉斐尔,崇拜他的时代,崇拜古希腊,尤其是神话股的希腊人;在音乐中,我崇拜格里格、莫扎特、海顿。我的藏书是二十来卷不朽的名作,所有这些使我的生活充满着魅力(1818年)。
因为我画画时力求精到,进度迟缓,所以挣钱很少。我很穷,工作也很勤奋,而且敢说是兢兢业业的。38年来我本可以积蓄将近一千个艾叩(法国古金币——译注),要知道我每天得生活。然而我的哲学,我对艺术的纯洁心地和情愫,加上我那聪慧的妻子的美质在激励着我,给我以力量,使我感到相当幸福。(1818年)
创作开始时只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而后只能博得少数人的欢心,一切都得强忍下去,这是艺术家的任务,因为艺术不单是一种职业,而是替人效劳。所有坚韧不拔的努力迟早会取得报酬的。我也将受到褒奖,那就是拨开乌云见青天。(1820年)
卓尔不群、洁身自好、知足常乐,这三者意味着真正的幸福。守身养心万岁!这是适当不过的生活准则,奢侈会破坏人们的心灵纯质,因为不幸的是,你获得愈多,就愈贪婪,而且确实总感到不能满足自已。摒弃那些所谓上流社会用以消磨时光的无聊玩意儿吧,朋友的圈子要小一点,要和你有同样的个人爱好和生活经验,都有从事艺术的情操;文学和科学能占去你的全部时间,使你成为一个非凡的新人。这种乐趣的源泉是取之不尽的。依我看,这样的人才是幸福者,有真知灼见,是名副其实的哲学家。(1821年)
我作画至今日(1821年4月20日),许多作品都不比别人的差,或许可说是全神贯注地完成的,但从来没有因追逐金钱而迫使我粗制滥造,由于我对待自己的作品过于精心,往往完成后在构思上不符合时代精神。最后,我终于明白我的作品被敌对者视为最大的缺陷,原来在于我的作品不像他们。我不知道道,我们之间到底谁是正确的,是他们还是我;问题并没有解决,看来要等待将来,由我们的子孙来作出公正的裁决了。尽管如此,我仍想让大家知道:我的创作在很久以前就只追慕一种范本——即是产生于那个光辉时代的古风艺术及其杰出的艺术大师们,拉斐尔为这一时代建立了一个永恒不变的艺术美的领域。我感到一种我确是在用自己的绘画证明我倾全力模仿他们的偏向,并继续走着他们所开创的那条艺术道路。
因此说,我是一个忠于他们学说的捍卫者,而不是革新者。但我也并非像我的刁难者所武断的那样盲目地模仿他们,我尽管卓有成效地运用14—1 5世纪的艺术学派,可是比前人观察得更全面一些。维吉尔善于从艾尼亚的陈词滥调中发现珍宝。纵然有人谴责我对拉斐尔和他的同时代画家的崇拜过于狂热了,我依然只在客观对象和这些艺术巨匠的杰作面前为之倾倒(1821年)。
我在精打细算我的高龄,它总是想报复我(1821年)。
不要以为我对拉斐尔的偏爱会使我变成猴子,何况这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我想,我在模仿他的时候,我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的。请问著名的艺术大师哪个不模仿别人?从虚无中是创造不出新东西来的,只有构思中渗透着别人的东西,才能创造出某些有价值的东西。所有从事文学艺术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荷马的子孙(1821年)。
多亏大自然赋予我以某些智慧,我得努力创出一条前进的道路,以便沿着这条路去求取知识,如果我觉得有时候我能取得一点进步,这是说,我已有所觉悟。我是什么也不懂的。自从我在那些高超的艺术中感受到其中的完美与伟大以来,确实使我体会到一种令人沮丧的优越感,它会使人坠入五里雾中,与其说是创作,不如说是我将毁掉作品。我首先热爱的是真实,我认为美只存在于真实之中,荷马和拉斐尔创造的那种真实是美的,所以我得不慌不忙地把我所学到的一切付诸实现。
与此同时,观者那种愚昧无知,也足以使我把最后一点自由时光消耗殆尽,弄得我几夜不眠。说实在的,所有这种苦楚和灾难就像爱情中的坎坷,或者恰当地说,像一种坚贞的母爱所招致的痛苦那样。偶尔的成功,不大的荣誉,或者一点或多或少的自满,都可以重新使你经受一种舒适的“精神折磨”(1821年)。
假如能用法律确立一项名目,授权去消灭我们这个时代的愚昧,我将是多么幸运啊,我一定能轻松愉快地从事我的艺术了(1829年)。
我觉得在我所生活的年代里,凡是不足惋惜的事物就不必沉湎于眷恋之中。我突然地移居罗马,对我说来是沉重的。我早就感到我和我的朋友间的深情厚谊,却没有想到可能深到如此程度,现在离开他们我总觉得若有所失……
是的,在罗马住了差不多一个月之后我才在各方面开始适应;我和我的前任院长相处得很融洽,但即使这样我也没有受骗上当,我仍将我行我素。这里有风度翩翩的大使馆官员,有能干的使馆秘书,我的领奖学金的学生们对我充分地信赖和尊重,我和他们也和睦共处;这里有设备舒适而齐全的房子,我的妻子以她素有的干练料理着这一切,直至财务,这对我来说是尤为重要的。总之,她免去我许多额外的负担,减轻我不少使我疲惫不堪的日常操劳,我应当引为荣幸的。当然,如果能把与之分别的人们忘掉,而又不为这些离别之情的思绪所苦的话,那我就眼前这种受尊重的称心地位更应满足的了(1835年)。
教皇利奥第七待我们可谓恩至礼尽了!古罗马卡辟托林山岗神殿内的维纳斯像,竟像一个犯丑行的妇女一样被藏到隐蔽之地——圣弥塞尔去了。若要见到它须经过特殊许可。一般地说这里所有行事都得经过许可方能办到。大葡萄叶子把男的女的雕像都覆盖了起来;公共建筑都在城堡内;圣保罗教堂按照瓦拉第埃的方案被不断地修饰着。一言以蔽之,就这方面看,罗马已不再是罗马了。古迹被风化,壁画在褪色,一切都不堪入目!宗教仪式和行列是平淡无味的,城里城外的色彩也很单调。到处是时髦的彩缎软袖子。一切在堕落,虽然如此,每人的脸是美的。古典美术作品还是那么宏伟。天空、大地、教堂建筑旖旎多姿,而凌驾这一切之上的,是拉斐尔的光彩夺目的艺术美,它是真正的圣物,它为人民所接近,整个罗马倚仗着它继续居于世界各大城市之冠,巴黎——则退居第二位(1835年)。
一位部长远道而来,找我谈关于为圣马格达琳教堂装饰壁画的事,并在他的亲笔信中建议我参加这项工作。我回答:“不。”我这样做是有多种原因的。我只屈从于我的内心意志:首先,我想在这已经住了六年的罗马住下去,现在我在这里感觉很好,假如将来再会引起人们的嫉妒,使我增加我总在躲避的苦恼的话,再作计议。我好容易克服了至今仍在刺痛我的心灵的那种对一切愤世嫉俗的感情。我宁愿做一个独持偏见的人,放弃一切我本打算在今后去做的事,所以我不能断然离去;还因为这些庞大的任务基本上得由我来接受,即是说,首先是交给我的……
这件工作不管怎么诱人,他们是出乎意外地感到无人能胜任这项任务之后才提议交给我的。当然,机不可失,况且一切又都是那样顺我所好。可是,唉!我怀着一种刺激性的快感喊出了这一声“不”! (1836年)。
我那几幅小作品《斯特拉托尼卡》和《小宫女》得以完成是出于我的自重,是为了尽我的职责。其实,这几幅画是小题大做了。我是以极大的耐心画着它们的。我很有耐心,不幸的是我往往会落入这种境地:即使这几幅画要耗去我的一生,甚至直到我死去,我首先感到满足的却是这些画。我从不轻易把我的画,尤其是仓促从事的画稿去滥竿充数,这好像我不愿做一件蠢事那样(1836年)。
虽然也有人多次好意地劝我:“赶快收收尾吧!别再重画了。”但如果说我的创作已大功告成或者说过得去了,那是在我20次重上画架,苦心孤诣地精心加工之后才取得的。以前是这样,显然今后我将永远是这样。我是否有检查自己的必要?让别人去判断吧。我是难以改弦易辙的。(1836年)
现在我感觉良好,罗马已完全把我吸引住了,要我提前离开这里,我会感到失望的。况且这里的霍乱可能会很快被扑灭的。据闻霍乱病确已波及屈拉斯特凡尔了。有人对我说,现在我回国的理由有了。不,我不能走。我们可以逃出罗马,但不能去巴黎。此外,目前我还是这里的“族长”(按指他是罗马法兰西艺术院院长——译注),我应当并且也愿意站好最后一个岗,这是不言而喻的(1837年)。
每当我们思念我们的朋友时(我的妻子和我经常这样),我们就憎恨这种流亡的生活。尽管它是多么优美,但这毕竟是名副其实的流亡。看不见自己的朋友,不能和他们共聚欢乐,这等于是处在半死状态(1837年)。
有人建议我给凡尔赛画画。为了不耽搁答复的时间,我说“不”,因为我已经下了决心,永远不为公众画任何东西(1838年)。
我很赞成拉封登的箴言:“对于恶人没有和平。”
巴黎正掀起一股攻击我的浪潮,指责说,近一个时期在罗马的领奖金学生的作品中有一种受我的影响的普遍倾向。这算什么,确有一定影响,我敢保证,任何一个院长,当然他不是列蒂埃尔,也不是坦维宁,肯定都会把自己的艺术思想作用于他的学生们的。至于我的影响是否好?是的,非常好,再好也没有了。我那倒霉的敌人是些伪善的骗子,他们是想用有害的教条控制一切!但已被我那真、善、美的学说驳得体无完肤了,他们是无法医治被我击中的创伤的。随便吧……尽管我还不大受公众欢迎,但是那些有教养的,甚至不大有教养的公众都在全面分析我的思想,我要请他们到法庭上去和我辩论。法庭最终不偏向我一边是不可能的。
我预感,我生命的余年将是惶惑不安的。那些走狗显然时刻在寻找机会想撕碎我,只要他们的魔爪还未夺走我的画笔,我将置之度外,做我该做的事。我暂时还得忍让,等待时机报复我的那些冥顽的诽谤者,这个时机一旦来到,我将揭露他们于光天化日之下。我愤怒,在这一群蠢驴中还有我的少数朋友,我是明白的,我有不容置辩的证据,总而言之这些朋友是在其间的。此外我就不知道,在这块我们如此孤独的地方还将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善良的朋友离开了我们,他们回家了,可是我们还得在这里度过漫长的两年,在此期间我真想再和他们见一面!大概有人认为,我可能被迫宣布与法国断绝关系,与我那美丽的故乡,与那块有我们舒适的栖息、之所的国土诀别。我已习惯于这种忧心忡忡的生活了,说实话,这种担忧是容易变成现实的。天哪!庸夫俗子们到头来,总是弹冠相庆吗?! (1838年)。
我在这里不很幸运,尽管这样,我仍要坚持到最后一天。我在计算着我能和朋友们重修旧好的日子,但是在巴黎,我只打算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除了音乐,我的内心世界以及可数的几位知友(很少,寥寥无几) 之外,我什么也不信任(1839年)。
无须赘述,我应当用眼睛盯着一切,包括任何决议给我所造成的困难等等。这个国家全然变了。从前的罗马,即对美术家从来是乐善好施的罗马已不复存在了。所有的大门都已关闭,使你感到事事都得央求,逆来顺受。我怎么适应呢!何况,拒绝是经常的。末了,我还得向自己的使馆提出要求和无休无止的抱怨,我虽也想维护尊严,但总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罗马的学校里有许多不足之处,我怎能不分青红皂白,也不能袖手不管。我就是这样身不由己地生活着。我终日忙碌,可总是受到冷遇。我想做一名称职的院长,切实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结果总要受到申斥,怨谁去呢?现在我的学生比过去对我更有所依恋,如果这点可以自我解嘲的话,也算是对我的一点鼓励。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将加倍努力,为的是有朝一日给我那些卑鄙无耻的敌人以回击(1839年)。
我那善良的妻子安慰并规劝我,竭力想帮助我摆脱这种烦恼,可是往事总使我悲愤欲绝,正像俄瑞斯特(希腊史诗:俄瑞斯特为替父亲亚伽门侬报仇,杀死了母亲——译注)一样,我自叹命薄,因为我在这里侨居已逾六年,所得到的只是悲观失望。我不打算列举这些接踵而来的重重障碍,来诉说我的悲愤原因。此外,尽管我忍辱负重,但还是有许多我无法克服的,而且敢说是一些不断被我证实了的麻烦。我不是泥塑木雕,相反,我是极其敏感的(1839年)。
我刚画完我的画(《斯特拉托尼卡》),就染上了疟疾。该死的疟疾!罗马和那里的水土是无法共存的。是啊,它已经不是我从前认识的罗马了!这里的一切都是难以忍受的。我在这里还要住五个月,第一个月过去了。幸好我未必再有时间去感受这里的忧患了,因为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完成三幅油画和其他许多事。(1840年)
尽管我感到无上荣幸,这是我有生以来允推独步的一次声誉,但我在日常生活中严守着一个美好的准则:“贵在自知之明。”我是素以此来鞭策自己的:我心里明白,只有那些确实有求于我而蓄意奉承的人才对我做那些无节制的赞颂,至于其他,我通通把它作为进一步完善我的创作的一服有效良药来吸取……并借此化为我得以扶摇直上的翅膀,不过我还要感谢上帝,是他赐给我这些成就的(1840年)。
我终于离开罗马了。只是在离别它的时候,我才感到无限惋惜。罗马如今对我们说来,是依依难舍的。天呀!我要和拉斐尔告别了,我简直像孩子那样地哭泣,热泪满面。谁知道我何时再能见到梵蒂冈?在此和我深为尊敬的朋友和学生们分手的动人时刻里,我怎能再说长道短,把我这些领奖金学生留下已使我深感不安。但同时,我也在思想上宽慰自己,不久我又将和另一些朋友见面,或许他们会更使我倾心一些(1841年)。
我接受了几件巨大的订件创作。我接受的任务很多,而且提交的方式是如此合我的心意,我不能不欣然说一声“可以”。也许是我重新获得了做人的地位,一切由此产生的成果把我推向社会的注意中心。我太忙了,以致把我六年来始终保持的个人自由都给破坏了。说实在的,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像从前那样有足够的勇气在动荡的艺坛上进行搏斗。六年中间我一直陶醉于自己的罗马法兰西艺术院院长(这已有所获)的身份的幸福之中,但是人们总爱否定我做的那些好的方面,或者是嫉妒它!尽管我对自己的新的地位有所惶惑,可是那些赞美、夸奖甚至向我作出的尊敬的表示统统都战胜了我先前的那种复仇心理。反正我在前进,一切悉听尊便吧!有一点大概我是有数的,即我的敏感在逐年地增强,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我必须全力克制,因为我若过分地激动,我就会立即轻率地作出决定,像逃走的让·德·尼维尔那样为人所不齿。目前我在为祖国服务,不想见异思迁,这里是我世界上最可爱的地方(1841年)。
有时我非常满意自己的创作,我觉得幸福。尤其是当我在隔了很长一段时间重新看到被我推向世界上来的这些作品时,这些由我的心灵生出的孩子不知费去了我多少心血,使我蒙受了多少辛酸(1841年)。
我住在巴黎,好像是一块被放在铁砧上的烙铁,每天被所有反对我存在的暴力捶打着一般,一下比一下更厉害。是的,这里我所见的和所听的一切,可以把我逼疯。所有这些无非想千方百计剥夺我的自由,而结果是,整个巴黎都教给我画画!……这一下几乎可以把形形色色的异己者气死,虽然如此,我仍安然无恙,如果不把那些小毛病计算在内的话(1846年)。
是谁可以在这里用语言和行为来亵渎我们崇拜的神圣的拉斐尔呢?啊,可恶的地方!如若我无忧无虑,如若那些与我的生活紧紧相连的周围的艺术对象全部消失,我将抛弃一切,离开这里……去哪里?去意大利?那里也有鼠疫。唉!我留在这里正是万不得已啊!虽然我在这里饱经忧患,但是说实话,这里也有我的朋友,抛开他们吧!这会使我更加难过的。(1851年)
我放弃了出席评选委员会的机会,会议是乱糟糟的,在那里凡是好作品都被占统治地位的舆论所扼杀,往后不会再有受推崇的获奖大作从那里产生了!评委会在名义上说是由九人组成,在那里,我作为资历较深的美术家却和一个怪胎推销员坐在一起……今天的全体会议竞通过了这个非法决定。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唯一准备的是:如果对我作出什么使我不满的决定,我将摆脱这个组织,放弃我的地位,丢开所有艺术创作活动,我杜门谢客,不如……用心画画,整天欣赏杰作,把我最后一滴心血浇注到艺术上去,做一个勤劳的闲人(1855年)。
我埋头于我的创作上,我热爱它现在胜过于以往任何时候。随着我的年事增高,我更加把画画看成是自己的迫切需要。我也觉得自己古怪,而且由于我接近暮年,似乎到了我该收拾一下自己的行李的地步。我希望这件行李是大的,并且越富足越好,因为我愿意活在人们的怀念之中(1856年)。
在巴黎我能做些什么呢?在这座倒霉的城里,艺术领域中一切最粗野、最荒诞不经的无政府现象令人绝望地猖獗着。在这里我不得不在温暖可爱的家中闲居,可是命中注定由我来忍受的烦恼依然朝我接踵而来,使我的生活充满着不安。看来我得改变一下生活方式。除了人格,现在我对什么都不加可否了,上帝保佑,好在我还没有失去自己对艺术的强烈感情和那几位我心目中难能可贵的朋友。凡是我深恶痛绝的事物,我将敬而远之,采取断绝往来的态度(1857年)。
现在我在精神上已显得如此衰老。一切存在之物的真正价值我是洞若观火的,我愿意活下去,并且只希望和自己亲密无间的人和事同欢共死,直到我只剩最后一口气,谁也不能剥夺我这一切。唯有这样,我才能从芸芸众生的敌视者中解脱出来,才能和那个不学无术、虚伪嫉妒、充满着低级趣味的社交界一刀两断,而更主要的是,我将不再受到经常败坏我的声誉的那种威胁(1858年)。
人们对我的责备也许是公正的,因为我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我的一些构图,不去创作新作品,而我是这样想的:凡我所喜爱的大多数题材的作品都应当去刻意求工,反复琢磨,或者像我在自己的早期几幅画上,比如在《西斯庭教堂》一画上所经常做的那样去精心对待。当一个美术家由于热爱自己的艺术并倾注了大量心血的时候,他就有权希望把自己的名字留给他的下一代,这时,他会孜孜不倦地尽力使他的作品臻于尽善尽美。伟大的普珊就是我的榜样,他常常在同一题材上翻来覆去。但不是去画蛇添足。有些作品确乎没有重复的必要了,恕我直言不讳,如果谁想再画一幅《圣西姆弗里昂》,我觉得是十分荒唐的(1859年)。
有人指责我固执己见,抱怨我对所有凡不属于古风时期或拉斐尔风格的艺术采取了不公正的态度。其实,我对那些不甚知名的荷兰和弗兰德斯画派的大师是非常推崇的,因为他们善于独到地描写真实,对于他们目睹的客观对象能表现得惟妙惟肖。不,我并不偏执,或者确切些说,我只是不能容忍一切虚伪(1859年)。
假如不是因为疏远了我的良师益友而倍感痛苦的话,我现在这种隐居的和热爱操劳的生活可以说是很幸福的,一本书、一支笔,再加上优美的古典音乐,足以使我心安理得了,愿上帝保佑,这支笔我将要握得更紧些(1860年)。
真是这样,到上个月末,我已经满80岁了,这不是开玩笑。你们之中不少人还是岁月方长呢,不过,尽管我上了年纪,我相信我还没有像许多别人那样丧失了理智。时光仍为我保存着智慧,使我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仅凭这一点也值得活下去(1860)年。
这顶金色桂冠即使是献给皇帝的,我也并不觉得它多么华贵,但是那两千个属于社会各阶层人士的签名却感动了我的肺腑。
在我这一生中,可以说好日子和坏日子总是交替着而来的,但坏日子更多些。这段时期我所经受的一切使我沮丧,使我愤懑,而且几乎久久使我陷入空虚,因为我身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具有青春的智慧与感情好动的人,他不仅不迟钝,甚至变得更加敏锐;这个人容易激动,缺乏耐心,并且指着这具羞与为伍的、老朽的、衰弱多病的肉体说道:“真糟糕!你这个呆头呆脑的笨蛋,怎么衰老得这样?”如果我的信仰和我那无与伦比的德尔菲娜的体贴照料也不能减轻我的痛苦的话,我一定是非常不幸的,即使有这些荣誉,有这个令人艳羡的炫耀地位也无补于事。
为了使我能从容地画完这幅巨作,我一生的至宝——《圣母》,我把它带到这里,带到芒克来画,这样我不至于疲劳过度,既能享受宁静的时光,又能利用我身上还有30年的精力,如果上帝果真允许,并赐我以这种垂青的话,在我奔向缥缈之地以前,我要竭力再增加几幅画。但愿上帝开恩,为子孙们再积些财富(1863年)。
我是祖国的儿子,我是真正的高卢人,但不是那些洗劫罗马和企图毁灭德尔菲的高卢人。现在在我们中间也还有这种人,不过,他们不是用武器去破坏,这些微不足道的现代高卢人是用他们的傲慢偏见和混乱不堪的浅薄知识去竭力诋毁自己的国家,百般摧折这个国家的真正艺术。他们在艺术的树下埋上地雷,他们像白蚁那样啃蚀艺术的精髓,他们无孔不入,直到把它弄成粉末为止。对于某些人我可以报以残酷无情的手段,但考虑到我重病在身,我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方式。而且我的不可动摇的信念和我对艺术那种谁也不愿否认的真挚情感证明我是对的……让人家去说我孤僻、急躁,古怪吧。既然我的一部分信仰来自于我的高尚的情趣,既然我所热爱和崇拜的一切往往被我证实是伟大的,那么很明显(不必借口我的神经过敏),我的所谓古怪是无稽之谈,又何必说我急躁呢(1864年)。
低能的鉴赏家,拙劣的美术家就像是一批地下钻出来的魔鬼,他们颠倒是非,破坏和控制着一切,我们,则充满着信心,至少在道义上胜过于他们。因为他们是瞎子,唯独我们这边看得一清二楚,他们比我们更加不幸(1885年)。
时至今日,那些异己的意见的威慑未能迫使我有半点退却。对我来说,荣誉问题只得让位于我先前的忠实信念了,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这种信念我也从未丧失过(186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