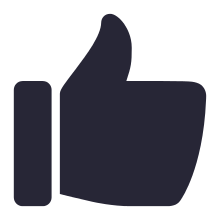女作家铁凝,是沿着文坛中尽人皆知的一条最为平坦、最为安逸的路走出来的。与她同时期的作家,因了那个时代的特殊性,也不乏一夜成名的神话,可像她这么早就少年成名,并且一生如此通畅的,只怕无法找出第二人来。
铁凝,1957年生于河北赵县
她生而早慧,也大器早成,是时人共奇之。出身河北高知家庭,18岁高中甫毕业,就写出了《夜路》、《丧事》这样超出年龄的力作,备受瞩目,并被作为文坛种子选手着力培养。等1983年的《哦,香雪》一刊发,那种与彼时文坛流行风完全异趣的大家风范,更是让她火遍全国。
她深受老作家孙犁的赏识。也正是在这些文坛耆旧的无私力推下,铁凝迅速当选为老家河北一省的文联副主席,成为那个时代几乎所有文学青年的偶像,亦或梦中情人。那是1984年的遥远往事了。那一年,她不过20来岁而已,花信年华,名位与文章,已是相看两不厌。
铁凝年轻时代
而在那一年,余华刚兴奋地从牙医调入海盐县文化馆,莫言还在为挣脱出农村艰辛地准备考试。王朔呢,这位1980年代中后期“最明星”的小说家,还整天在火车站那里溜达,倒卖点车票,做着朝不保夕的黄牛生意。
只可惜,这世上之事,最忌讳的就是个十全十美。树上的果实,一旦熟透,马上就要坠落,月满则亏,凡任何人总要稍留欠缺。
一个完美成功者的叙事,往往会开端于一个惨烈的失败,铁凝也不能例外。据说——只能用“据说”这个词了,铁凝在事业上大圆满,可在感情问题上,“丁香暗结意中情”,始终是位“苦主”。个人情感问题,本是私事,不值一提也不该一提,可这也几乎是文学界人所共知之事了,也没什么不能讲述。并且,我要谈的重心,不在八卦,而是感慨,就连文学之业,其实对女人也要比对男人更残酷。
写出《第二性》等作品的法国女作家波伏娃
人类自有“女作家”以来,从狄金森到波伏娃,从李清照到张爱玲,从杜拉斯到余秀华,不管古今中西城乡强弱,你是湔裙梦断也好,是不念无畏也罢,总过不了男女欢爱这一关卡,似乎也没有不遍体鳞伤的。而你又不能缺失这种由爱恨情愁磨碎而出的养料,碾出文思,悟出世情,汇为深吟幽歌的作品。世间万事,唯有情感的碾压,最会融入一个女子的血脉,彻底改迁她的文学基因。飞絮飞花何处是,层冰积雪摧残,疏疏一树五更寒,这是所有女性作家的文学宿命。
德高望重的河北老作家孙犁,是早期赏识、无私栽培铁凝的文坛大佬之一
2007年,媒体大张旗鼓报道铁凝终于结婚的新闻。那一年,她已经50岁了,我都还在上学,食堂中放下碗筷翻《南方周末》专文,还兴致勃勃地跟对座美女童鞋讨论,这位号称中国文坛头号的美女作家,两鬓都能找出多少缕白丝来。她结婚的对象,是名经济学家华生,那些知音体文章依旧渲染套路,说她为此“等待了16年”云云——可这些终究只是说给大众听的吧,所有文学界中人都心知肚明,她确实无怨无悔地等了16年,或者更长的多,可别有隐情。
当年报道
她等的对象,根本不是华先生,而是另外一个同样名声显赫的某男作家。一位作品惊世骇俗,性情也放浪形骸的年长作家,等他,也许就像在等候一艘在软红欲海上下沉浮、时隐时现但永不会朝她靠岸的不系之舟。
我常想,不去体味这种深藏若虚的经历与苦痛,恐怕永远难以理解铁凝,无法去读懂她的文字吧。
比如,《玫瑰门》里的叶龙北,《没有钮扣的红衬衫》里的安静,《大浴女》里的方兢,她所有小说里的人物设置都犹如“自叙传”;比如,她《大浴女》里对女人身体炫耀式的描述片段,尤其是借助书中人物所写的“这一段故事”:女主将作家情人写给她所有信,全烧掉并且纸灰兑水喝进肚里,据说这是惊心动魄的“实录”;比如,《无雨之城》、《玫瑰门》等书中总爱搭讪上有妇之夫的感受描写;比如,很多作品里,都出现的那位劳改犯出身的文化名人等等,都可说是死水微澜式的追忆吧。
名动一时的作品《哦,香雪》
而铁凝自己,也在她散文《女性之一种》中这么讲过,“人们通常的看法,女性的自赏意识终要强烈于男性。身为女性,我不免也受了这通例看法的传染”。这位身相庄严,气质上予人以特别尊贵并坚韧的女作家,论世俗事业的成功,可谓打败了所有男性同行,但是情感的依托上,似乎依然摆脱不了那位男性同行“灵与肉”的纠缠,以及“绿化树”的笼罩。
镜头回溯:1991年5月的某天,铁凝在京,冒雨看望冰心老人。“你有男友了吗?”冰心问。“还没找呢”,铁凝低声回答。“你不要找,你要等”,90岁的冰心,定睛地望着她说。铁凝铭记下这句话。可一等,就是16年,那个浪子还是没有回来,但是祸福难明,她也随之等来了近10部作品,还有海内外瞩目的中国作协主席的文坛至高位。
北方另一位同辈“美女作家”迟子建,64年生在黑龙江漠河
花盛则谢,光极则暗。这到底是幸是命,当事人甘苦自尝,传闻明晦难辨,我们不好去偷窥一二。只是我总觉得,这段经历作为女人来说,固不堪回首,但是身为作家,她确实应当感谢这段生活额外奉送的阅历。因为这段悠悠心绪,她得以作为一个倾诉者、一个抒情者、一个歌哭者、一个狂笑者、一个祝福者亦或呐喊者,把自身也放进了小说里,将脉搏、微笑、眼泪、祷祝及滴在心头的血,一并与文字搅拌。
一个优秀的作家,尤其是天资本就卓绝的女作家,当她身心可与书中的人物,互为代言人的同时,一部部的杰作尾随而至,是最可预期的。
由铁凝,我还应该并且常常想到的,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文学命题:清贫助笔,名利伤才。
与文坛名人余秋雨
2006年11月12日,铁凝当选为中国作协主席,顺利但并非没有争议。这是中国作协成立近一个甲子以来,迎来的首位女主。那时,不知有多少人为她欢欣鼓舞,也不知有多少腹诽流行在喧哗之中。但是现在回首,那些掌声也好、嘲笑声也罢,几乎就是欢送的一致预示:这位优秀的女作家,在被名利包围的同时,实际也差不多已被文学缪斯所抛弃了。
写作,毕竟是一个最关系心灵与精神的事业。所有最可怕的写作生涯,都莫过于落入自我与外界制造的俗套,身心一入此套子,灵府就必然蒙尘铺旧,会像工艺品那般,日久渐浸,失去灵动与情感,尸居余气,形神之离,不过就是时日多少的计较,不足虑矣。也可以说,对于任何作家而言,阻碍创作最大的阻挠因素,往往有二:其一,是“江郎才尽”;其二,便是被“名闻利养”所包围。
近20年来,作品不断的上海名女作家王安忆
前者,是一种自身内在的才思的枯竭,每一个写作者都将不可控地,或短暂或长期参演这出人生悲剧目。而后者,则意味着身心被低级趣味、庸俗难堪,可能是泥沼般污浊的生活,所重重围困。灯红酒绿,子夜歌阑,销魂时刻,窗门大开,苍蝇纷进,是每一桩灵魂都难以抵挡与提防的腐蚀案件。为此而文思荡然,风流歇竭,是古已如斯,也是为时下无数才子佳人所验证的——看看韩寒、郭敬明、蒋方舟,这些年他们都写了什么?
大概也因此,自2000年出了长篇大作《大浴女》,并随之坐上作协副主席大位之后,作家铁凝,实际已逐渐辍笔。在被扶正之后,其写作生涯,更是“无画无诗只谩夸”,再也没有什么可观作品可贡献于世了。偶尔有所涂鸦,不过是天低衰草、芦荻风残中的信笔酬应,着实不值一哂。倘要追溯渊由,这到底是因为 “椅上人”没有惜寸阴挤的写作闲暇,还是作为“哥德小姐”过于养尊处优,早已才思洪退,我们也是不得而知的。
同样不得而知的是,当“作家铁凝”渐行渐远渐无书,换来“铁凝主席”觅官千里赴神京时,是幸是命,应该也是一个与铁凝有关的,另一个得不到解答的曝日清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