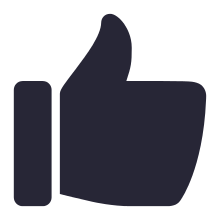荷兰人民报(Volkskrant)专栏作者Corina Koole收集荷兰女性婚姻的故事,今天以《Chinezen scheiden niet, had Chan geleerd, dus bleef ze te lang getrouwd》(陈知道中国人不会离婚,所以她结婚的时间太长)为题,采访了一名化名为陈(Chan)的荷兰华人中年女性,让她讲述她的爱情与婚姻故事。
以下是本文的翻译。
28年来,陈(43岁)仍然嫁给了一个她无法与之交谈的男人,一切都是因为她要保护家庭的荣誉。
我的父母是荷兰的‘第一代华人’。如果我的母亲不喜欢什么,作为女儿的我们有时会挨打,但她永远不会解释她为什么不喜欢那样东西。华人社区很封闭,感情问题从来没有被认真谈论,没有人互相求助,也没有华人接受(荷兰的心理)治疗,但是却有很多的八卦。
在我们的家庭中,只有两件事是重要的:好好在学校念书,好好地结婚嫁人。
我的姐姐早早带着一个荷兰人回家了,我的另一个姐姐嫁给了一个突尼斯人,最后的希望落在我身上。作为最年轻的女儿,我必须确保与华人结婚,在大型的婚礼上宴请来自中国各地的宾客。当我在假期工作期间,在一个度假农场的厨房里遇到一个中国的男孩时,我还是个少女。虽然他不会说一句荷兰语并直接从中国来,但我坠入了爱河。
我觉得他很英俊、风趣而又甜蜜,而最重要的,他让我有机会给我父母他们想要的东西。五年后我们结婚了,我的父母为婚礼亲自邀请了客人,那是些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人,但我很高兴父母可以挽回了过去失去的面子。
父母一生都在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国家,在朋友和家人的餐馆里努力工作。我要全力以赴地证明他们是有回报的。我的这种愿望非常强烈,即使在我在不同城市学习的那些年里,我每天晚上都规规矩矩地把自己锁在学生房里。其实,我也大可以穿着短裙和到外面喝酒,但我没有这样做。好像我父母的眼睛穿越了人类的极限,如果我进入了一家酒吧,他们会立刻知道,而我会立刻遭到报复。
同样的忠诚也用在对我的丈夫身上。我们有两个孩子。他也在只讲中文的中餐馆厨房中工作,就像后来他自己经营的寿司吧一样,只讲中文。
他拒绝学习荷兰语。他工作,回家,躺在沙发上,每天都一样。
我在家中负责与外界的联系。我到学校开家长会和老师交谈,和孩子一起决定上什么的中学,做家中的行政工作(收到各种荷语信件之后作出回复,并处理账务等)。我想,假如我能够在星期一早上和同事讨论星期天晚上的电视节目“Wie is de Mol”,我想这是很开心的事情。但可惜,家中我们从来没有看荷兰电视台。
最严重的是,我没有与丈夫分担我的烦恼,我们没有互相讨论任何事情。在我们整个28年的婚姻期间,我们只讨论过日常的家务琐事。我觉得这是很愚蠢的,但我几乎不能责怪他,因为他和我接受同样的教育,家丑不要外扬,但也不在家中吵闹。
中国人不会离婚
我一年又一年地和一个男人在一起,名义上一对结了婚的伴侣,实际上,在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后几年,我知道我们必须离婚。
我承认,屈服于命运与屈从父母一样,毫无意义。中国人不会离婚,当你们互相厌倦时,会分开睡觉,然后外部没有人会知道这件事,说三道四的了。
但我在荷兰出生长大,和任何人一样都是荷兰人,只是完全纠结于我的华人情感和婚姻触角。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想说什么,现在是我的时间。不过,当我父亲在2016年去世时,我觉得不能伤害他。
我很不情愿地告诉了我的姐姐和荷兰女友,我想要离开我的丈夫。现在,我的孩子长大了,我有了更多的时间,我想去剧场,去电影院,过着真实的生活,但我的丈夫不能,他不可能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2018年的一天,我焦急地做出了决定。在没有对我丈夫说什么的情况下,我选择了一个地区的律师并预约见面了。我用冰冷的手按响了门铃。律师在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他孩子的照片,代表了一个我不熟悉的世界。我说:我想离婚,我该怎么办?
几天后,他给我丈夫写了一封奶油色纸上的信。我在家门口的垫子上找到这封信,扣下了,想在带着孩子回中国度假六个星期的时候才交给他。当我丈夫读信的时后,我不想在那里。
回到家后,我指望会有激烈的反应,但却没有。我的丈夫打开了这封信,当然无法阅读,因为总是由我处理官方文件,所以他要等我回家才能看。
我仍然害怕他会拒绝,我一直等他,并把律师文件推到他的眼皮底下。他不假思索地真诚地签了名,只有在三个月后我们的婚姻正式结束后,他才明白我做了什么。
当然他觉得自己掉进了一个陷阱,这是对的,但我说,我还有其他选择吗?一个你从未与之认真交谈过28年的男人,你能怎么样?评估我们的婚姻已经太晚了。现在他终于离开了,我第一次有空,找了一位不是中国人的精神心理医生,让他帮助我解决内心的困惑。
我很高兴,当我和其他人交谈的时候,我不再低下头;我16岁时想穿的鞋子和短裙,现在穿起来仍然很舒服。虽然我有时不得不反思,我的父亲从来都不喜欢这些东西。(黄锦鸿编译)